魏德东教授:刍论中国佛教的公益事业
魏德东
“如来世尊福足、慧足”,佛陀所创建的佛教也是一个并重世俗幸福与宗教智慧的宗教。佛教自创始起就关注众生的世俗生活,并由此发展出丰富的公益理论和实践。
关于佛教公益事业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研究领域。就印度佛教社会学来说,较为重要的着作有早岛镜正的《初期佛教と社会生活》,古正美的《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1993年),Greg Bailey 和Ian Mabbett的The Sociology of Early Buddh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等。关于中国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通史方面有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と社会福祉事业》,竺沙雅教授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2),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世纪的着作有《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台北:商周出版,2003),谢和耐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黄敏枝的《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1934~198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游彪的《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刘长东先生出版的《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2005);有关清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近着有杨健的《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随着大陆宗教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宗教公益事业成为一个研究热点。200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与河北天主教进德文化研究所合作,举办了“首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随后出版了“宗教公益事业论丛第一辑”《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1],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2008年10月,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举办,主题是“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论文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2部着作收集相关论文约60篇,从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公益理论、实践,宗教公益事业的法律环境、国外宗教公益事业的经验等各个方面,对宗教公益事业予以了集中探讨,其中约有1/3的论文直接论述佛教。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将“当代宗教公益事业的区域比较研究”选为基金资助项目。
本文的目的,是在吸取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佛教与公益事业的关系为中心,界定佛教公益事业这一概念,勾勒佛教公益事业的理论基础和古代实践,简述人间佛教与公益事业的关系,最终指出佛教公益事业的当代意义。本文的核心命题是,佛教拥有深刻的公益事业理论,具有丰富的公益事业实践,佛教公益事业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社会根源,对于人间佛教的形成发展和未来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佛教公益事业的涵义
公益事业,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业。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救灾济贫、扶助残障等慈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活动;(4)其他公共与福利事业。(中华,1999)[2]
理论上说,任何部门都可以从事公益事业。在中国,传统上公益事业的主体一直是政府。不过,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民间力量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公益事业中,并形成专门的公益组织。这类组织并列于政府和企业,被称为社会的第三部门,起着对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我们所说的佛教公益事业,指由佛教团体或佛教徒组织、负责的促进公共利益的非赢利事业。在组织上,目前中国的佛教公益事业大多数由宗教团体直接经营,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性公益组织。
有关佛教与公益事业的关系,在当代中国一直存在争议。在佛教界,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是,佛教就是传播信仰的,公益事业可有可无。与此相应,在政府方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佛教过多地参与公益事业会人为地扩大宗教的影响,需要加以限制。
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地区为中心发生了8级地震,死亡人数8万以上。史无前例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万志愿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之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而中国佛教界也空前地参与其中,反映出中国佛教界的公益意识达到了新的水平,而佛教公益事业的价值也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肯认。
二,佛教公益事业的教义基础
公益事业是一个现代概念,然而,佛教公益事业却拥有着深厚的教义基础和丰富的历史实践。以解脱众生为目的的佛教,从来都重视大众的公共利益,将信众的世俗利益和神圣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与其弥补了中国社会中公共空间的空白有直接关系。
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缘起说,认为世界是一个相关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世界观落实到伦理学层面,形成了业报因果理论,主张善恶有报,“诸善奉行,诸恶莫作”成为佛教徒的基本要求。而佛教的公益事业,作为善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经典中都有深刻的阐述。
佛教的公益事业理论,集中体现在佛教的事业观、慈悲观、福田观和布施观等方面。
“事业”一词,来自佛教,其基本含义约类似于今天慈济功德会所说的“志业”,多指有神圣价值的工作。就含义指向来说,佛教经典所说的“事业”与我们现在说的公益事业,颇为接近。大乘佛教的奠基者龙树在《大智度论》中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意思是一切能够有益大众的事业,都是佛道,可以说把世间具有正面价值的工作,都纳入了佛教的范围之中。而这样的具有佛教意义的事业,也就具有了神圣价值。《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三归依赞”,更提出,“利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利生,也就是利益众生,和弘传佛法并举,成为佛教的根本工作。
在佛教所倡导的事业中,医学、科学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部分。释迦牟尼被称为大医王,运用医疗救助众生。佛教有所谓五明的说法,其中包括工巧明、医方明。工巧明属于科学技术的畴范,后来的佛教在修桥补路等方面多有建树,应该与此有关。医方明属于医学和治疗,也是佛教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大乘佛教还认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最高的智慧。
慈悲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慈悲观就是佛教对慈悲问题的看法。在佛教的众多教义中,慈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特别对于大乘佛教来说,基于其普度众生的追求,慈悲观甚至是最核心的教义。
据大智度论卷四十、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五等载,慈悲有三种:(一)生缘慈悲,又作有情缘慈、众生缘慈。即观一切众生犹如赤子,而与乐拔苦,此乃凡夫之慈悲。然三乘(声闻、缘觉、菩萨)最初的慈悲亦属此种,故亦称小悲。(二)法缘慈悲,指开悟诸法乃无我之真理所起的慈悲。是无学(阿罗汉)之二乘及初地以上菩萨的慈悲,又称中悲。(三)无缘慈悲,为远离差别之见解,无分别心而起的平等绝对之慈悲,此乃佛独具的大悲,非凡夫、二乘等所能起,故特称为大慈大悲、大慈悲。
慈悲的基本含义是与乐、拔苦,而其最高表现叫“无缘慈悲”,指没有分别的绝对的慈悲,又称“大慈大悲”。《大智度论》卷17第27品《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就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则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悲相连,包含了人生所需要的与乐与拔苦两个向度。
慈,有时又被描述为佛、觉悟,也就是佛教的根本理想。《大般涅槃经》卷14说:“慈即如来,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大藏经》一二卷,698页下)。《大智度论》卷27说:“佛以慈为首。”
“悲”,有时又被看作是获得最终觉悟的途径,是智慧之母,是一切功德的基础。《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说:“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佛教的慈悲观,就是佛教徒对慈悲内涵与意义的看法。佛教认为,慈悲是佛教的根本教义。《大智度论》第27卷又说:“慈悲为佛道之根本”。《观无量寿经》则说:“慈悲为万善之基本。”[3]《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4]
如何落实慈悲呢?佛教提出了“福田”思想,指明了实践慈悲的途径,对于中国佛教的公益事业影响很大。
福田,是一个比喻,指能产生幸福的地方。如同农民种田,可用收获一样,播种你的善行,则可以收获幸福。这些被播种的地方就被叫做“福田”。《探玄记》6说:“生我福故名福田。”《无量寿经》“净影疏”说:“生世福善如田生物,故名福田。”
在佛教中,能够生出幸福的地方很多,因此有二福田、三福田、四福田、五福田、七福田、八福田等种种说法。不过,从根本上说,福田可以分为2类。一是“佛及圣弟子为福田”,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开悟者,对他们的供养会带来很大的福报。这可以说是福田的本义。另一类就是以众生为福田,如父母、师长,特别是贫穷者。这一类福田的价值趣向,与公益事业有密切的关系,是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中国佛教史上,西晋翻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最接近今天的公益事业的思想。该经提出“七福田”的说法,认为应该为这7类福田布施,具体内容是:
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这是号召做一些佛教建筑,属于福田中的第一类。
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这是指植树造林,修建水库之类的活动。
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是指医疗卫生事业。
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这是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五者“安设桥梁,过渡嬴弱”。这也属于公共交通事业。
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这是指在道路的近处挖井,以方便干渴的行路人喝水。
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这是指建造公共场所,讲究文明卫生。
显而易见,在七福田中,后面的6种福田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在时隔1800年之后,这6种福田依然毫不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部《像法决疑经》,又称《济孤独》,对“二福田”思想有简要的界定,强调了救济贫穷的重要性,对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佛教公益事业影响深远。第一,布施、救济穷人是成佛的原因,“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第二,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两种,敬田是佛、法、僧三宝,悲田是贫穷者、孤寡老人乃至饿狗、蚂蚁等动物。令人吃惊的是,经中明确提出,布施的根本对象是悲田,悲田重要于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一思想,显示佛教的福田思想具有超越自身的普世精神,具有利益一切众生而不管其宗教信仰的追求,是佛教公益事业开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与福田观相联系,佛教又提出了布施观,是实践慈悲的具体方法。
布施,是指将自己的所有,送给他人。《大乘义章》卷12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掇己惠人曰之为施。”在佛教中,布施是最重要的实践方法。《像法决疑经》认为,布施是成佛的根本大法:“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在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种实践方式(六度)之中,布施第一;在吸引大众信仰佛教的4种方法(四摄法)中,布施为首。
布施的具体内容,佛教中不同的表述,有二施、三施、七施、八施、十施、三十七施等多种说法。究其根本,布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财布施,就是用物质财富救济贫穷的人;二是法布施,指以正确的道理指导人生。
佛教的布施观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反对将布施看作寻求利益的手段。布施需要有3个条件,这就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法界次第》卷下之(上)说:“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财物,三事和合时,心生舍法,能破悭贪,是为檀。”[5]檀,就是布施。布施最重要的要求是“三轮体空”,也就是对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物品,都不执着,不斤斤计较,这样才能起到布施的作用。如果给了人家东西,就念念不忘,或者寻求得到回报,都是不正确的。佛教因此有所谓“布施偈”,说“能施所施及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胜心,供养一切十方佛。”(见《心地观经》)
正是基于独特的公益事业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业领域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自传入中国,就特别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修桥补路、挖井、医疗、救济等多种事业。宋代,则形成了专门的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长期负责公共事业。如维护桥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则以一定的田产作为补偿,称之为“守以僧,给以田”,[6]颇有今天美国布什总统将社区公共事业委托给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意味。黄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分为5类,实际上这也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史,分别是(1)桥梁的兴建与维修,(2)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3)道路的修建等,(4)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5)公共墓地、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7]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则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8]。
此外,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也许是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公共的社会空间。上层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负责。底层则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家族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制度。然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社会,终究具有极大的缺陷,很难超越血缘基础,为更广大的公共利益服务。在这种历史处境中,以出家生活为基础,同时具有普度众生情怀的佛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社会这一固有缺陷。[9]也许正是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国与慈善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佛教的中国化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国固有社会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担者。
三,人间佛教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佛教的面貌也为之大变。一种带有创新性而又不失传统本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对现代公益事业给予高度重视。现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大成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并在90年代以后为大陆佛教所吸取,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生动活跃的篇章。
无论是否认同人间佛教这一概念,20世纪上半叶,积极开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基本共识。最早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太虚大师,突出“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意义;被视为传统力量代表的圆瑛大师,创办了以抚养孤儿为核心的大量公益事业;而慈航法师则将“文化、教育和慈善”这3大公益事业,称为佛教的救命圈。
太虚大师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论证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大师已经“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10],孕育了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如何具体“实行”?太虚大师提出要在风俗建设、国民教育、医疗事业、幼儿养育等方面,服务社会,救世利人。他说,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11]。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
20世纪上半叶,圆瑛大师在佛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圆瑛大师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时,即创建僧、民二校,僧校用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来免费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开始,圆瑛大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免费教养,历时近30年。
公益事业之所以为现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现代形式落实大乘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负面的,被看作是落后与寄生的代名词。因此,佛教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现代需要,别开生面。慈航法师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说法,影响深远。他说,“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12]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是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起步阶段。这一伟业真正开花结果,是60年代以后的台湾。其中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扬传统旗帜的僧团,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业。
星云大师是当代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代表人物。1967年,星云大师创办建佛光山,提出“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等四大宗旨,其中文化、教育、慈济和共修这四大方面,都包含着公益事业的内容。在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图书馆、美术馆等设施和机构,编篡了《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藏经》,发行《人间福报》,翻译白话佛教等。在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了4所大学,在台湾有8所社区大学,全球有近50所中华学校,另外还有18家佛学院。在慈善方面,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募集大量资金赈灾。在共修方面,通过遍及五大洲的百余家道场,将中国佛教的禅修经验奉献给全人类。所有这些,都具有超越佛教自身的公益属性,进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影响世界的集中代表。
佛教公益事业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慈济功德会。这是一个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慈善团体,在全球宗教慈善团体中都堪为翘楚。其领袖证严法师是印顺导师的少数剃度弟子之一,其领导的团体以在家居士为主,核心是从事公益事业。慈济建有一流水准的慈济医院,有闻名遐迩的骨髓库,有专业化的救灾团队,还办有慈济大学。印顺导师圆寂后,媒体的报道是:“印顺长老虽没有自己的僧团,但奉其为导师的证严上人等弟子却创立慈济、把‘人间佛教’发挥到极致。”[13]
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很自然地被区分为保守派和开放派,前者指更为重视恪守传统,后者表更乐意与时俱进,并无褒贬之分,如美国的基督教就大致分为主流的自由派和保守的福音派。在佛教中,也有一些僧团以保持传统为重,如重视禅修的中台禅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宗教公益事业。实际上,保守性的宗教团体往往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比如中台禅寺,在全世界对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群弘扬禅修文化,本身就有公益事业的色彩。而中台所办的小学、中学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具有极高的水准。
台湾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教授在台湾宗教与公民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在台湾,成为公益事业核心的力量并不是西方人想当然的基督教,而是佛教,如慈济功德会,佛光山等。魏乐博教授认为这体现了佛教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功能的转化。[14]不过,佛教所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或许本就是佛教固有的传统。
中国大陆佛教经历了更为曲折的过程,但公益事业一直是其重要理念。自20世纪末开放以来,大陆的佛教公益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是佛教公益事业的积极提倡者。他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30周年时说,“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们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优良传统。”[15]
大陆的佛教公益事业,约略包含以下几种类型。一者扶危济困,二者捐资助学,三者医疗救助,四者护生环保,五者文化事业。另外,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公益事业的佛教组织,日益成为佛教公益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职业的佛教团体有60多家,省级机构10多家,地市县级机构40多家。”[16]
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地区为中心发生了8级地震,死亡人数达8万以上。史无前例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万志愿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之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而中国佛教界也卓然奋起,参与其中,反映出中国佛教界公益意识的全面提升。佛教慈善事业的价值也前所未有地鲜明地走进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视野之中。
在佛教界的救灾实践中,可以看出许多佛寺和佛教团体平时就积极参与扶危济贫等慈善公益活动,在观念、组织和条件上都有较好的积累,因此能够迅速有效地投入到救灾之中。最为着名者如什邡市的罗汉寺,在素全法师的领导下,不仅安置了上千灾区,而且将禅房变为产房,在寺内建立起临时的产科医院,接生了108个孩子,成为佛教普渡众生的最生动体现。[17]而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上海龙华寺、河北省佛教协会、河北柏林禅寺、广州光孝寺、庐山东林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灾区,以组织化的形态投入到救灾当中。
20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佛教界的杰出表现,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中国佛教史上,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佛教发展的成就,亦为中国佛教的进步开启了新的航道,其历史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现。
四,佛教公益事业的意义
无论是悠久的佛教公益事业历史,还是记忆犹新的佛教抗震救灾,都证明佛教团体从事公益事业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而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多重现实价值和意义。概括地说,佛教公益事业既可以满足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的特殊需求,也有益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亦可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构以及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佛教公益事业能够满足大众的某些特殊需求,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众所周知,政府以及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从事公益事业,特别是政府更有民间团体所难以企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可或缺的价值吗?回答是肯定的。佛教公益事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以一定的宗教思想为指导,因此会创造出一些具有特殊人性关怀的活动方式,净化大众的心灵,提升社会的良知,发挥其他团体的公益活动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举例而言,佛教公益活动中对皮肤接触的意义的强调,就具有特殊的慰籍功能。慈济功德会在帮贫济困时,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做“肤慰”,即要求慈济志工亲手为流浪老人洗脚、手上擦油、剪指甲等。依据慈济的说法,不仅仅在四月初八为佛像浇水是浴佛,为老年人洗澡更是浴佛。而在实践中,无论是被关爱的老人,还是关爱老人的志工,往往在皮肤接触的一刹那,都发生心灵的震颤:被爱者为慈济人的大爱所感动,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曾为自己洗过脚;慈济人则觉醒了内在的慈悲,许多大老板贵妇人在握到干柴一般的手掌之时,心会顿然柔软下来,慈悲溢满心田。这是一个爱的互动过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均衡,更是爱的传递。
在佛教中,关于肤慰,或可归于四食理论中的“触食”。触食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接触外境时,所产生的喜乐等感受,认为这些感受具有长养身心的功能。这其中就包含了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会引发心灵的感应,本身就是人类成长的食量。从这类佛教思想中引发出来的佛教公益活动形式,与那种仅仅给穷人一些金钱有很大的不同,有其特殊的精神价值。
再者,在当代中国,参与公益事业是佛教发展自身的最有效途径。置身于一个非宗教人口占多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宗教徒一直处于人口少数派的地位,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自身,通过何种途径扩大影响,是当代中国宗教团体面临的共同课题。从最近20多年的发展看,参与公益事业是提升佛教社会形象的最有效方式。公益事业包括扶贫、助残、救灾、环保、医疗、教育等丰富的内涵,参与此类活动,会降低不同信仰间的张力,最大可能地扩大自身的影响。
佛教团体进入慈善事业领域,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宗教、跨信仰,成为不同宗教、信仰间相互理解的桥梁。以慈济功德会为例,其中的志工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无信仰者,甚至还有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慈济的公益事业中找到了共同点,同时也改善了大众对佛教、宗教的认知。
第三,当代中国的佛教公益事业,可以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任何宗教团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语境当中,只有引领时代精神,才能在为社会的进步奉献力量的同时,赢得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与佛教公益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相应的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通过佛教公益事业,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当代中国宗教的重要历史使命。
宗教团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非赢利组织之一,是培育公民思想的摇篮。在谈到美国的民主与政治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美国人民,特别是黑人等下层人民在教会中习练了民主,教会是美国社会民主的培训场。宗教人类学家魏乐博教授通过对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认为以慈济为代表的佛教团体在公益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为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作出了贡献,成为台湾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宗教完全可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大陆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中,专业性公益组织的出现最具研究价值。这类组织中所蕴含的自愿、透明、廉洁、奉献意识,恰恰是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所难以实现的。这些价值所具有的普世性,最终将成为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重要资源。
--------------------------------------------------------------------------------
[1]张士江、魏德东主编:《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2]参见《***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第3条。
[3]《大正藏》卷 21,页484上。
[4]《大藏经》卷2,页717中。
[5] 《大正藏》卷46,页686中。
[6] 参见张雪松:《试论佛教承办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保障与优势》,见《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论文集》第145页,厦门南普陀寺2008年11月印刷。
[7] 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413-434页。
[8] 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1934~1984)》,何兹全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9]元代史官黄溍(1277~1357)曾生动地描述家族世袭与佛寺传承的异同:“凡佛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庐赀蓄器械百须之物,悉得以为世业,传子若孙,其成之难而保有之不易,与齐民之家固无大异也。然人之子孙不皆才且贤,而佛氏之子若孙率以义合,必择焉而得其才,乃以畀之,故其传往往至于千数百岁而不坠,世家大族弗如也。”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卷13,《净胜院庄田记》,页129上-下。
[10] 何建明:《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返本开新》,见《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论文集》第145页,厦门南普陀寺2008年11月印刷。
[11] 太虚法师:《第十编学行》,《太虚大师全书》,印顺文教基金会光碟版,精18,页31、32。
[12] 慈航:《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佛教人间》第4期,1948年2月,页49-50。
[13]《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台佛教界精神领袖印顺长老圆寂》,新加坡早报网 2005-06-06。
[14] Robert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Westview Press, United States: 2001.
[15] 《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稿》,第30 页。
[16]张云江,《中国当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见张士江、魏德东主编《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第19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17] 素全:《512汶川大地震记:我的108个孩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0420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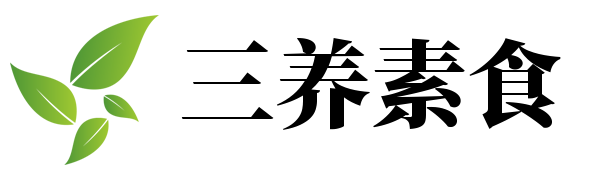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