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佛教的经济理念与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经济问题之审视
佛教的经济理念与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经济问题之审视
周齐
内容提要:佛教经济是广被关注的问题;但佛教的经济理念与敬义的逻辑关系,与世俗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仍有待梳理和深入研究,释迦牟尼由出世修行而觉悟成佛,标示了佛敬离俗修行而觉悟脱苦的发端。早期僧人行四依法,受供养,不蓄财。僧伽有余建无尽财以备不时。然佛教发展,钱财问题无可逃避,遂逐渐形成合乎义理逻辑的解释及经济理念。中国环境下。供养及乞食的保障性差。寺院经济於北魏初成,唐宋以降更趋成熟、布施、佛事,田土和寺户,及长生库、碾皑、商店等,皆为寺院财利来源;但也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农禅经济。凡此,由僧不蓄财,到僧伽建无尽财,再到形成寺院经济等,佛教经济形制变化很大。佛教经济既促进佛教发展也成败坏佛教之渊薮。本文由佛教义理及戒律为进路,大致疏理了佛教义理在经济理念方面的解释及逻辑残索;拜结合有关发展史,尝试说明佛教经济的关键在其宗教特性,佛教与经济是佛教宗教性与经济世俗性不断调试的动态平衡关系。
关键词:佛教义理经济理念宗教特性
佛教虽然是一个特别标榜出世的宗教,但无论如何,它不是这个世界之外的宗教。事实上,佛教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关系密切,更不要说经济这个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基础的重要方面了。佛教与经济的关系,无疑是直接的和密切的。
历史地看,也恰恰因佛教是特别强调出世的和清净的解脱修行的一种宗教,佛教的经济表现,就常常使得其陷入其所标榜者和其所表现者的矛盾中,此亦是常被世俗社会所诟病之处。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几次由帝王实施的灭佛事件,多数也主要与佛教经济问题有关。自古至今,佛教经济都是佛教发展中很突出的问题和重要方面。尤其现今社会,经济炽热,佛教亦概莫能外地被经济热浪笼罩,交织着现代社会巨大变化的佛教经济现象和相关问题,亦随之增温而被热烈关注。
然而,佛教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经济?是否有相应的经济理念?与佛教教义有怎样的逻辑关联?佛教经济与世俗经济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还是比较含混而有待进一步明确理论。不过,虽然相关佛教义理与经济理念、及佛教与经济关系的义理研究和论述仍显缺乏,但已有不少相关历史上寺院经济的具体研究成果;而且,虽然佛教作为宗教有其特殊性,以及佛门有其相对的封闭性,使得此类问题不易疏理和透视,但佛教教义和戒律的资料和研究却很丰富。因而,无论如何,佛教经济的相关理论问题是个有必要正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也是有条件和进路可以尝试探究的问题。
基於相关问题意识和研究条件的考虑,本论文由佛教发端发展的义理和历史践索为切人口和进路,以期对佛教基础义理与经济理念形成的内在理路和逻辑关系进行疏理和分析,并结合进入中国社会後的相关变化,尝试从一个角度对佛教经济理念和佛教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有所揭示。
一、基本教义戒律与相关经济理念的内在罗辑及其界定
佛教与经济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理念关系,或许首先还是要溯源到佛教的发生机理上,虽然这样难免因长足回溯造成的条理和论述的艰难,但显然,就疏理佛教经济理念与教义的关系起见,这样的回溯则是必要的。不过,由於这样的回溯,在此也有必要说明,就佛教发端时期的义理和相应的经济理念而言,使用经济这个术语也似乎过大,能涉及的或许应是一些相关范畴的理念,诸如相关简单财物、金钱、分配等方面的一些基础看法,然而,不可轻视地,这些也正是佛教基本经济理念的发生基础。
1、与觉悟脱苦之修行目标相一致的佛教经济理念基础
由佛典所说,当年释迦部落的王子悉达多出离世俗生活,是由於看到现实社会中的人生诸苦,遂决意出家修行以寻求解脱之道。其行脚参修许多年,尝试了多种途径,但却没找到满意的出路,以致其最终放弃了那些修行,定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终於获得觉悟,从而有了自己的一套对於解脱之路的认识和方法,佛教从此创立,释迦部落的悉达多王子成了释迦牟尼佛。
概括看,释迦牟尼指出的是一种通过主体觉悟而达到超脱人生之苦以求得解脱的宗教理路和方法。其所谓的觉悟,大致标的的也是个体存在与所谓宇宙存在之根本实相相契合的境界,由此角度看,似乎并没有超脱古代印度源於《吠陀》思想资源的“梵我一如”的思想脉络和痕迹。但是,显然,他有不同於当时其他宗教流派的解释理路及修行方式上的特点。
佛教由聚焦於人生世间之苦而发端,希求由超脱三界不再参与轮回,以达到解脱诸苦的目标,目标的达成就是要实现与根本实相的契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即意味着究竟实相之外的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要略去的,更何况究竟实相之外的一切就是产生人生世间诸苦的根源,後来佛教还有理论解释这一切如何是假,是空。可是,对於众生而言,要略去的一切既不假也不空,而是生活於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於是佛教用“缘起”理论及逻辑来解释世间万象,即所有一切,包括世间诸苦,都不过是因缘聚合,无自性,所以是“假”,是“空”,即所谓如梦幻泡影。不过佛教开始时似乎更注重如何实在地解脱苦,概括的基本原理是“四圣谛”,即,苦、集、灭、道,所谓要明了世间苦及诸苦所由之因缘,明了诸苦何以可减之原理,明了由之修行可以得道得解脱。
按照诸苦之因缘逻辑,人生有诸苦是因为没有觉悟,还蒙昧在无明愚昧中。而愚昧中最根本的就是贪、瞠、痴,所谓“三毒”。众生若要不苦,可通过修行,迷离因无明愚昧造作出诸苦的世俗世界,禁戒三毒,减少和最终超脱诸苦,达到觉悟解脱。不过,摆脱诸苦的修行并非易事。诸苦被概括为“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对、求不得、五阴盛,这些苦,真可谓无一是世间众生能逃脱的。所以,坚持出世的禁欲的或者少欲的清净修行以求解脱苦难,是佛教及其教义的基本标签。这种标签不仅通过其理念标榜出来,更通过有戒德的行为表现出来。
事实上,关於解脱,佛教发展有精致的逻辑和周详的解释,以及很多种途径的修行方式。不过其发生机理大致如此。循着这样的践索,可比较方便地了解佛教在处理所谓经济问题时大致可能采取的态度和选择,以及可能陷入的困境。
一些寓教於事的经典故事和戒律,比较能说明早期佛教的一些状况,反映着释迦牟尼时期的佛教和跟随其出离世俗而加人佛教的修行者们,是如何尽可能地让自己和同修们禁戒世俗欲望以提升精神境界,尽可能地实践一种不同於当时其他教派的、既生活简陋的却又净行高尚的修行生活。
仅举衣着之例,开始时有各式各样的衣着,世俗讥笑沙门衣着如同王子大臣淫欲之人。佛陀遂教导徒众应齐整衣着。但齐整衣着并不是要华丽衣着,而是相反,是粪扫衣。但是,虽衣衫破旧却要衣着齐整,不失威仪。既不同於那些骄奢淫逸的王臣,也不能像一些外道那样不雅。即所谓,心中无欲,得粪扫衣即如同得第一服。
诸如此类的节俭生活而高尚戒行的要求,在《阿含经》及《僧只律》等经典多有讲说。僧人的行止依照的是所谓“四依法”,即,粪扫衣,乞食,树下坐,陈弃药。如此要求,可谓执行的是最低生活标准。虽然戒律中没有特别明确讲不蓄财,但其解脱义理和这类物质消费克俭至极的行为规范已显示,基本无财可蓄,甚至可以说,因为无财乃至没有财这个概念,因而,也就没有蓄不蓄财的问题。
由此见,在佛教的发生过程中,早期修行者的观念和行止,基本是尽可能地把觉悟得道的解脱目标之外的所有一切事物和要求都降低到最简最低的状态,精神境界和戒德修行高尚。而世俗也多是由这些方面来比较和褒贬佛教沙门与其他教门的,做得好的沙门就会受到尊重,就被称为大德。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而这个圣人的神圣特性,就是出离世俗来修行脱苦之道,并觉悟得道。这也就标明了,离俗修行,觉悟脱苦,是佛教的一个基本宗教特性。
不过,也正是那些有丰富故事的典籍及戒律说明,脱离现实的欲求是很艰难的,即使对於那些已经出离了世俗去实践解脱修行的沙门们,禁戒欲望和世俗需求仍然是那麽不容易,而且,每每成为修行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问题。於是,遇到什麽问题就解决问题,并逐一形成规定或法则,亦即积累成名目繁多的戒条。释迦牟尼去世後,门徒弟子们结集佛说,最早结集的大概就是戒律。戒律不仅是维系佛教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准则,实际也是佛教所根基的教义模式结构中的一面重要基础和支撑。
因而,大致可说,降低和禁戒世俗欲望的禁欲生活,摆脱产生诸苦之各种世俗因缘,追求精神的升华和觉悟得道,是佛教发生机理的一个基本逻辑链条。相应的,佛教早期的所谓经济理念就是修行者尽可能地远离、不涉及、或者是不直接涉任何经济。
2、与禁欲出离之修行实践相关联的佛教经济理念取向
事实上,那些戒律反映的模糊史迹也显示,作为个体的禁欲修行和佛教整体事业的发展,始终都回避不了经济问题。
个体出家人保障生命之基本所需,主要靠托鉢行乞和布施。僧众形成僧伽,佛教影响扩大,信奉者益多,布施随之增多应该是可能的。对於个体僧人和已发展成集体的僧伽而言,无论行乞还是布施,都可能产生剩余问题。如何处理剩余财物,便是一个能反映佛教发生时期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方面。
在此节录一点佛教戒律中关於受施和处理剩余的片段,由此可大致透视当初佛教生动现实的僧伽生活,了解早期佛教的相关观念。
一则是“花法”和“果法”,即对布施多余的花和果的处理。“汝日日与我尔许鬉。余者与我尔许直。得直已,得用作别房衣。若前食後食。若犹多者,当着无尽财中。是名花法。”“果法者。……果若细者当量分。若以手为限。若大者如多罗果、昆罗果、椰子果、娑那沙果、庵婆罗果。如是等当数分。若多者应与贩果人。日日应与我尔许果。余者与我尔许直。得直已,应着前食後食中。若犹故多者,当着无尽财中。”这是说,布施的花、果,多余的可以换得钱,用於住房穿衣之资和前食後食之资,若仍有剩余,则应当放“无尽财”中。
所谓“无尽财”,即“子母展转,无尽”之意。戒律典籍中的解释多如此:“《僧只》云:供养佛华多,听卖买香油。犹多者,卖人佛无尽财中。”“《十诵》:僧只塔物出息取利,还着塔物无尽财中。佛物出息还着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等。”即,布施等所获的剩余物资,变卖所得,形成僧伽集体的基金,以备弥补衣食之资,尤其寺塔修葺之用。
在印度那样的自然环境下,僧人个体修行,物质消费大概还是能降得很低。但作为集体的僧伽的运行,尤其佛教事业的发展,没有金钱的支持显然也是不行的,且不是由剩余花果变现积累的“无尽财”可以支撑的。一则精舍布施和接受的故事即反映了早期僧伽发展中的这个问题和解决方式。释迦牟尼成道後宣讲佛教,赢得信众,便有大檀越为其设立道场。即如佛传故事所透露,在释迦牟尼居留较久的舍卫城,就有大檀越为其安置的道场,叫“只树给孤独园”。事情大致是,富商给孤独长者诚信佛法,欲购波斯匿太子只陀在舍卫城南的花园,作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说法和驻留的场所。只陀太子先是不以为意,刁难长者,要其用金钱铺地为代价,长者即不惜倾家荡产以金铺地,太子终为其虔诚所感动,亦将园中林木奉献给释迦牟尼,故而得名“只树给孤独园”。但其中释迦牟尼及其僧团并没有直接得金钱布施,也没有涉及交易,只是被提供了一处止息基地以传播教法。
按照佛教出世的修行旨趣,僧人通过出世和禁欲的修行来尽可能地摆脱世俗诸苦的羁绊,以求达到终极觉悟的目标。所以尽可能不参予俗务而专事修行,即使免除不掉的一些俗务也由俗人替代。有戒条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规定僧伽可接受“净人”处理俗务。在戒律中有则“众生法”,处理的是布施众生可否接受的问题。文曰:“佛言,一切众生不听受。众生者。象、马、牛、水牛、驴、羊、麖鹿、猪、奴婢,如是及余一切众生,不应受。若人言我施僧婢,不听受。若言我施僧园民妇,不听受。若言施僧奴,不听受。若言施僧使人,不应受。若言供给僧男净人,听受。……若施净人为料理僧故得受。……若言供给尼僧女净人听受。……若施净女人为料理僧故得受。……若受众生者,越比尼罪。是名众生法。”这是说,众生布施中,唯净人可受。
供以“净人”可以接受,为的是僧人不可杂务,不可自捉污秽物等。故而,僧伽中,行侍粥饭,清理卫生,打水,生灭火等等,皆由净人为之,即所谓净人制度。由此亦见,佛教出家人保持清净迷离世俗,是佛教戒行中注重强调的方面。事实上,出离世俗不仅是早期佛教在德行方面标榜与其他教门不同的方面,也是後世为教内外视之为重要德行的一个标准。僧俗有别,僧不蓄财,是相关佛教僧人戒行的一种普遍的认识认同。
不过,出家人并不等於得道者,所以,修行者仍会有贪欲,也会涉及财物所有和分配等问题。如《僧只律》中有则“种树法”,是说佛住舍卫城时,“尔时有比丘,於僧地中种庵婆罗果,长养成树,自取其果不令他取。诸比丘言:‘汝何故自取遮他?’答言:‘我种此树护令长大。\’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佛言:‘此种殖有功,听。’一年与一树。年法者,若比丘僧地种庵婆罗果树、阎浮树,如是比果树应与一年取。若树大不欲一年并取者,听年年取一枝,枝遍则止。若种一园树者,应与一年。若言我欲年取一树,亦听。若种芜菁,若葱,如是比菜应与一剪。若种瓜瓠,应与一番熟取。是名种树法。”虽然交涉的财物不过是树和果子,但这也算是一种产权和利益分配的关系问题。判断的结果是,种树者有功,但僧伽公有土地上种树,应允许取果,但取要有度。
透过戒律中的类似故事看,早期的所谓财产问题大多是果子花树等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资,不过,即便很细小,仍要处理,且关系重大。其遵循的义理理路,是通过少欲知足的信条,以限制个体剩余蓄积,并以充公或均分的方式,来禁绝欲望以及遏制可能的欲望膨胀。可见,早期的理想僧伽,大致以出离世俗,解脱修行,四依法等诸多基本信条为要求,以求尽可能地断除贪欲及诸种可能造作诸苦而成业障的条件。佛教僧众基本不与金钱直接交涉,出家人不直接参予经济俗务。
由此见,佛教所树立的其宗教神圣性,很大程度即是由这类高尚世表的修行、寻求终极觉悟解脱的基本教义特徵而得以标榜和确立,因而,可以说,与出世脱苦的教义指向相应的不涉足经济活动的经济理念,也是佛教凝聚其宗教生命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内容。
3、舆发展需求之义理解释相协调的佛教经济理念模式
显然,目标不等於现实,出家不等於得道,禁欲不等於无欲,而且,超越现实的修行和关怀现实的发展,乃至其神圣性的落实等等,实际都构成佛教与经济关系中的诸多悖论。佛教的经济理念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不断调整中整合。
如前文所叙,大致佛教早期几乎没有蓄不蓄财的问题,那种不留剩余的托鉢行乞、树下坐、粪扫衣、陈弃药的修行生活,几乎已然涤荡了财乃至财的概念。明确的不蓄财之说,倒似乎是与菩萨观念相联系,如《大涅槃经》讲修菩萨道若要无众生般烦恼的妙法之一,就是“不得受蓄八不净物”。所谓八不净物,大致是“蓄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手自作食、不受而啖,污道污威仪,损妨处多,故名不净”。乃至“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这是以潮水不过限比喻这个限制,而且重要程度,比生命还重。
再如《大智度论》中有说,“出家菩萨守护戒故不畜财物”,“以戒之功德胜於布施”。因守戒而获得的功德,故可以匹抵和胜过布施,不必蓄财而可得布施。这裹的布施应是指财物布施,因为佛教的布施除了财布施,还有法布施和无畏布施等。似乎也显示布施原本是双向的,修道者也要施布施,而不仅是受布施。不过,在这个布施链中,出家菩萨的戒德则成为获得布施的资格或者等价物。
的确,布施似乎更像个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只有信众对於三宝(佛、法、僧)的财布施功德的一面被突出强调,而出家菩萨不蓄财物的方面也基本上流於理论,因为事实上,接受布施的直接承接者就是僧,或者说就是出家菩萨们。因而,如何对待布施和受施内容等问题,尤其对於钱财布施的处置和态度,应是佛教经济理念的一个关键环节。
世俗方面或有以为,讲清修出世的佛教应与金钱多无交涉,但佛教典籍显示,佛教很久以来就不讳谈金钱;当然也同时显示,一如金钱在世俗社会的作用,金钱不仅是佛教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同样是败坏佛教的一个罪恶渊薮。至於什麽时候开始可以接受钱财布施,大概难以确定,也只能透过相关佛教戒律经典来了解一些信息。此列举一二。
《弥沙赛部五分律》有则佛陀降伏恶大象战胜调达的故事显示了受施金钱的一个因缘。佛教中的佛与调达,即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与魔王。故事说,一时调达在还没有觉醒仍是恶王的阿阇世王辖内,为了对付佛陀,在佛陀将要行至时,唆使象师放醉恶象冲向佛陀。佛弟子相信佛陀乃人龙道尊者,象必降伏。诸外道则认为象力胜於人。遂积敛金钱共赌胜负。“醉象遥见佛来,奋耳鸣鼻大走向佛。阿难怖惧恍惚不觉人佛腋下。佛语阿难:‘汝向三闻无苦,如何不信,犹作此惧?’佛见象来,人慈心三昧,而说偈言:‘汝莫害大龙,大龙出世难。若害大龙者,後生堕恶道’。象闻偈已,以鼻布地抱世尊足,须臾三反上下观佛,右绕三匝却行而去。从是已後遂成善象。”“国中人民无复恐怖,何其快哉。诸外道辈皆悉惭愧。佛弟子众踊跃欢喜,敛得金钱七十余万。”
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典籍,也有很多跟金钱布施有关的故事。如,一婆罗门长老闻听一僧人讲佛法後,非常欢喜,对僧人说,“大德坐夏了日,我当奉施六十金钱。”僧回答,“无病长寿即为咒愿。今所施物施心璎珞。”僧人为了长老要布施的心意,为其祝愿,并称赞其心意如实贵的璎珞。又,一贫家子希求生天,有圣者告之,若得此福,可用五百金钱作饮食,供养佛僧。贫子母告之,付师受业之束修尚不够。贫子遂拼命佣力,虔诚感动雇主,不仅付佣金五百,而且提供场所作饭食供养佛僧。适逢有商人过,随喜而得饭饱。其中商主得知此贫子实乃其熟识一长者子,遂送财宝与之。贫子则认为其只为生天而饭僧,无求财物之心,拒之。商主说,其中任何一宝都可作百个供养。你既然信佛,就去问佛是否可受吧。贫子遂“往诣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设供尚有余食,与五百商人皆令饱满。时彼欢喜,以众多珍宝见惠於我。为受此物为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缘此宝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花报。果报在後\’。时长者子礼佛而去,为受珍宝”。此所谓“花报”,是指因为前因而得的回报。“果报”则是今生造作之业而决定的来生报应。
如此看,信徒布施钱财是为了获得希求的功德,受施者得到钱财,则是为了达成布施者的愿望,因为得道的佛乃人龙至尊之出世,法力可作用布施者的因果业报;出家菩萨“守护戒故”,能够“以戒之功德”来达成布施者的愿望。
这样一种布施—功德—因果业报的逻辑关系,使得金钱在佛教中的运行有了宗教神圣性意义上的合理性解释,金钱在其中因宗教意义而被纯洁化。更由於布施功德和因果业报的联系,布施成为来世业报好坏的一个因由,使其更具有了宗教决定性力量,实质上就是使得钱财布施的宗教性意义被提高。这样一种逻辑关系的形成,或许是既保障佛教标榜出世清修宗教目标、又可落实其现世发展之需的一种解释理路和解决方式,也是後来的佛教发展中处理钱财关系及相关经济理念的一条逻辑钱索。
二、中国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经济理念
传人中国的佛教,由於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调试,经历了一个在新环境中适应、溯源和整合的发展过程。但,佛教依然是佛教。
1、中国环境的寺院经济及其经济理念与义理基础
中国大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四季分明,主要靠夏秋收获为食,是靠天种地的依赖程度很重的农业社会,使得在印度等热带地方可行的完全靠托鉢和自然物产维持生存的条件大打折扣。对僧徒而言,现世这个生命皮囊的维持方式,首先就不得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虽然“佛家遗教,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行乞等头陀行仍然实行;依靠布施供养也还是生存物资所得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供养人”的形象很早就出现的佛教壁画中即是例证。不过,乞食环境差异性大,可依赖程度低;即使供养,保障程度也很成问题。
而且,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环境,也让僧人的行脚乞食的游走受到诸多限制,乃至游僧常被视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当政者大多要求僧人修止於寺院,以方便管理。即使信佛的帝王也不能容忍“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下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违者加罪。”对於借着修建功德而竞相靡费钱财,也多有限制,认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饬令,若“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自今一切断之。”
资料显示,以土地乃至经营商业来保障寺院的生计,即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寺院经济形式和趋势。史料中最早的由朝廷推出的寺院经济定式,是北魏时期对於僧只户和佛图户的设置,由当时著名的僧官沙门统昙曜提议出台的相关佛教经济政策,不过,或应说,这种政策大致是对已经在佛门流行的相关不规范做法的整顿和正式制度化。
《魏书·释老志》称,北魏和平(460—465)初,僧昙曜官任沙门统,奏请,“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於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只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矣。”
这种寺户制度使得寺院经济堂而皇之提上台面,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僧只户或佛图户形式的制度或被停止或被改造,但类似的寺户制度实际上仍然广泛流行和被延续。比如由於有较多出土文献,敦煌地区古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即显示,相关寺院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丰富,其中寺户制度是寺院经济相对稳定的重要保障。而且对於寺户的成分构成、规模、及人身自由度、分配方式等,也形成相对细致和严格的分类和管理。
再如,晚清时一部基於《百丈清规》的注疏,列有接受施田的详细程序:“接待施主,……住持命侍者请两序班首及知会客堂、库房、***,知产,齐到方丈酬谢施主。即写舍书,以为凭照。施主、住持及在会者,俱签押。并给原契券,亲供。粮串、税票,俱收齐。住持上堂说法,以报施恩。事竟,在会众人与施主同往看产。随带竹签十余枝,以插标记,使界限分明,不得浸混他界以致争讼。每年春季,会两序众执,同看界限一次。当年监院将舍契报税。即过寺户,勒石,人万年簿。”可见,寺院接受田土布施,役使寺户,获得维持生计之资,是中国历史环境中一直普遍流行的一种佛教寺院经济模式。寺田除了皇帝赐田,多是接受信徒布施田土,作为斋田。虽然寺院规模不同,维持生计的经济形式差异也比较大,但以来田土的寺院经济方式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维持生计的方式。
逻辑地看,寺户制度之所由出,大致是因为寺院要以田土为生计之依,但又由於佛制戒律,僧人不能从事耕种等世俗杂务,接受的施田,即转由寺户耕种。而信徒要成就布施功德,田土布施也自然成为一项布施内容。相关研究也有说明,寺户制度可能还是佛教戒律中净人制度和魏晋以来客户荫户制度杂糅的一种结果。但无论如何都显示,佛教进入中国环境後在生存方式上有了一些适应性调整,不过相关经济理念仍努力保守着佛教基本义理所标的的取向,至少形式上还刻意保持僧俗有别的理想界钱,以及以修行平衡布施的交换逻辑等,但寺院经济依然是僧伽生活的重要部分,尤其寺院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义理解释的困境,或许也应看作佛教发展的促因。
2、寺院经济的扩大经营及其经济理念与义理解释
虽然斋田是寺院的一个基本生资来源,不过,并非佛教寺院经济的唯一内容和形式。曾几何时,佛教寺院还被允许从事一些商业经营。尤其是“长生库”的经营,使佛教寺院经济的经济经营的程度加深。所谓“长生库”即是以信众布施的钱财为基金,而设置的一种信贷业务。也叫寺库、质库、解典库、解库,及无尽藏等。
建立无尽藏的目的,教有典制,如前文所及,所为衣食和塔寺之资。因而成为信贷性质的经营则是逐渐发展出来的。史称,梁武帝时,曾“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已利益无限。而每月斋会复又於诸寺施财施食”。又如宋代《宝云院长生库记》曰:“住持莹公坐席未温,首叙巾盂以估於众,得钱一百万,内外道俗又得钱百万,太师魏国史公捐国夫人簪珥以施之。合为利益长生库。以备岁时土木钟鼓无穷之须。後五年建大讲堂。”可见,用於救济,尤其寺院维护和营造,仍是建立无尽藏的主要初衷和目的。再如,研究著作中最常转引的是唐代《两京新记》中的一则,即武德年间长安化度寺所建之无尽藏院而至富可敌国的事例。化度寺获得经营无尽藏,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於武德、贞观及武则天时期,曾多次提供天下寺院修缮之资,普施天下僧众,分施天下饥馑。这样的布施效应,又引得城中士女争相施舍钱财於寺院,乃至有车载钱帛弃下不留姓名者。不过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也再次引来麻烦,唐玄宗时将之毁灭。
不过,化度寺无尽藏被毁,但经营无尽藏乃巨大获利途径则昭示於世,有能力的寺院经营无尽藏长生库大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知何时,寺院的长生库已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钱庄及典当行。宋代诗人陆游有文字记录此现象,其谓,“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後赎苎还,於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之。”至清代,状况依然。如樊榭山房主人亦靠典当於寺院长生库来周转拮据开支。其有诗曰:“青镜流年始觉衰,今年避债更无台。可知子敬家中物,新付长生库里来。半为闺人偿药券,不愁老子乏诗材。敝裘无恙还留在,好待春温腊底回。”在元代,甚至有皇帝下旨保护寺院的相关经营不为强力者剥夺。有则圣旨即曰:“但属寺家水土、园林、人口、头匹、碾磨、店铺、解典库、浴堂、竹园、山场、河泊船只等,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这般宣谕了。呵别了的人每要罪过者,更这的每有圣旨,麽道做没体例句当,呵他每更不怕那圣旨。”这类事情,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干过,其曾不止一次地亲自料理京畿大寺的经济纠纷,也曾下旨勒石为戒。
事实上,寺院经济其实很大程度一如世俗经济,都是利益目的下的经营,因而利益之争是常事。如唐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即曾於雍州“与僧寺争碾硙”。所谓“碾硓”,即磨房,唐律中颇多涉及碾硓的律条,可见碾皑也是一个利润高的营生。在宋元以降的佛教寺院中,碾硓跟长生库一样,是寺院经济的重要内容。不过这些还属於正常状态下的经济活动。在一些非常时期,鬻牒,即卖度牒,也是佛教经济的一个非正常的经营内容,而且往往恰是应朝廷募集资金的要求,且多有发生。而这项交易的结果,一般是佛教或某派因此获得拿了钱财一方政治力量的扶持。
当然,佛教寺院经济中最基础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来源,是佛事活动。佛事活动是展示其宗教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同时也是有可能败坏其宗教形象的一个直接方面。佛事活动之大者,是为国祝厘;通常的即是为百姓的宗教需求服务的经忏之类。但是,宗教性却往往会在这类最频繁发生的佛事活动中被消解,问题即由於经忏佛事往往流於寺僧挣钱牟利的营生。历来朝廷若有佛教政策出台,必要有很重的篇幅来约束佛事活动。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亲自过问佛事活动的价目表。经营经忏的寺僧,一直都是既为社会所需,又为社会所鄙的一个部分。显然,问题不出在经忏,而是一般的从事这类佛事活动的寺僧忽视或没能力在宗教神圣性的问题上有较多的考虑,而确实是拿经忏作为营生。
由此见,佛教经济的发展,有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之基本需求而从事的因由,更有与世俗一般经济一样的目的,因而有与世俗社会政治经济等扭结在一起的同构的部分。虽然这类通过接受施田以及经营长生库等维持寺院经济和佛教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仍然不外是在布施—功德的逻辑关系绕索上延伸。但是佛教经济经营行之即久,神圣的宗教外衣往往裹不住经济的世俗实质的膨胀,从而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性间的张力加大,矛盾加深,从而引出诸多困扰,或者陷入困境。
虽然自北魏至五代都有来自朝廷的剧烈的减佛行动,且多由经济问题引起,但作正面的义理解释却并不多。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经济义利是个吊诡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社会无处不有义利问题,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重复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义的教条。佛教知识分子似乎也多不谈经济义利,也或许,这在佛教而言并不是矛盾的问题。不过,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教派起伏整合的过程中,对於修行形式和实质之类的问题讨论很多,比如落实在所谓权实等方面。菩萨道及方便行似乎也颇为受到推重。对於佛法与经济问题议论得明确直接的是确立中国第一宗派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智颉。其在解释《法华经》的几种著作中,一再在所谓“自行之权实”,的义理意义上明确解释“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的经义。即如“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治生产业中亦可得道。历史地看,开权显实的菩萨道,亦权亦实的方便行,似乎很得追捧,在隋唐间兴起的佛教宗派大多都有相关解释。在这个角度看,佛教经济即佛教的治生产业,亦可看作和解释为追求觉悟之道的一路修行方式。显然,问题关键不在佛教产业发展与否,而在於佛教在治生产业这一路上所开之权与佛法之实是相即、还是相背。
3、农禅耕作的经济模式及其经济理念与义理逻辑
不过,有田土有寺户有长生库乃至碾硓店铺等多种经营的寺院经济,并不能涵盖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所有形式。中国地大差异性亦大,社会环境也变化多端,佛教的实际境遇自然会影响着其生存状态的调整。
虽然按照佛制戒律,僧人不得耕种和自作衣食等。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中,不仅常有饥乏之忧,还常有人祸之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就发展出了倡导自己耕作满足衣食的一种寺院经济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之为“农禅”,或被描述为“坐作并重”,也是中国环境下产生的一种佛教经济理念和形式。
这种佛教经济形式,兴起於隋唐时期的禅宗丛林僧团中。背景应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导致许多拒绝还俗的僧尼或速避尘嚣,或逃向南方。但寄食无地或聚众後难以为继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湖北黄梅,後来被尊称为禅宗四祖的道信的僧团,相聚山居者居然有五百多众,显然不可能靠布施维持。资料称,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与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五祖弘忍为徒时,即是“画则混迹驱使,夜便坐摄至晓”。而且正是因为其“常勤作役,以体下人”,遂为“信特器之”,成为接班人。这种通过劳作来支持寺院经济的形式,到唐代百丈怀海时,即成为一种“普请”制度,即“上下均力”,“集众作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後即延革为一种丛林制度和理念。
应该说,形式上这是一种突破传统戒律的佛教经济制度。而且,即使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僧人“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也是被视之为“无益於时政,有损於治道”的事情。但是这种劳作制度似乎并没有在教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困扰,相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促进。审视看,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劳作和修行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个突破的可能性,是因为一些僧人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修行者可能达到的觉悟,即主体自性与宇宙究竟实相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主观契合,没有特定的外在限制可以匡定。即如智者大师有关於治生产业与佛法实相的解释,有关於权实关系关联的菩萨道和方便行的解释等。禅宗最杰出的觉悟者六祖惠能自己就是作务行者出身,但其说法语录却能被尊奉为经。其也强调,“法元在世间,於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在理论上对修行实质和修行形式问题作了开拓性合理性的解释。所以,为了能打坐修行而进行的劳作,进而也成为等重於打坐的一种修行途径。即所谓劈柴担水间亦可见道,“鳜头为禅杖”,“蓑衣准布袍”。“牵犁曳地”亦可“法法全张”,所谓随处可见道得道。
後来的禅宗还产生了以强调劳力而弘扬教法宗派,如云门宗等。到晚明时期,仍然有骄傲地坚持劳务而光大门庭者,如曹洞宗的无明慧经,“入山躬自作务,力田饭僧。鼎建梵刹大小十余所,皆……一鳜之功也。”慧经直说:“山僧……若不履践百丈堂奥,焉能禁得大众?”其坚持躬亲劳作,不仰人鼻息,营造数刹,影响甚大。如其住宝方寺,即“四方闻风而至者,络绎於道,挂搭常数千指”。
中国佛教中产生的这种相对自主的寺院经济的经营形式,对於佛教发展影响很大,意义也很大。独立的经济可一定程度地保护精神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这也正是追求觉悟的佛教所要求的基本的主体条件。减少对於世俗权利的依赖,也更有益於维护佛教提倡的离俗清修的宗教特质。在这个角度看,这种形式上有背戒律的佛教经济,似乎更显示了佛教基本教义的本质意义。无明慧经就被尊称为“古佛”,即表明这种作风更能反映佛教根本取向。
二、结语
如是观之,一方面,就佛教自身观之,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佛教经济理念和佛教经济的实际运行,的确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也反餹社会以很多影响。但是可接受的变化和调试,其实没有在根源性上发生本质变化。佛教经济模式,不外是在其基础教义上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自身悖论的不断调试整合。而调试的尺度,则把握在其宗教神圣性与经济世俗性的平衡性,以及义理解释的合理性方面。
另一方面看,经济就是经济,所遵循的只可能是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之所以称作佛教经济,即如同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等,只是因为有其各自的特点而已。佛教经济的特点就在於其是宗教经济,是具有宗教特质的经济。因而,体现了佛教宗教性特质的经济,就是佛教经济。不然,就难免会受到质疑。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经济事例也说明,淡化了宗教性的过於世俗和过於膨胀的佛教经济,或者打着宗教幌子变质为世俗经营的所谓佛教经济,往往就是致使佛门遭到指责乃至打击的根本因由。
由以上所检索之佛教的经济理念和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经济,大致可见,佛教和相关佛教经济的发展虽然与社会及环境息息相关,但作为一种宗教,其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关键还在於其本质的宗教性的延续和发扬的如何。社会接受和认同的,仍然是其体现其宗教根本性质和普遍意义的方面。因而,其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平衡,应是佛教经济运行和佛教经济之合理性的重要平衡尺度。佛教与经济,即佛教宗教性与经济世俗性不断调试平衡度的动态平衡关系。
(摘自《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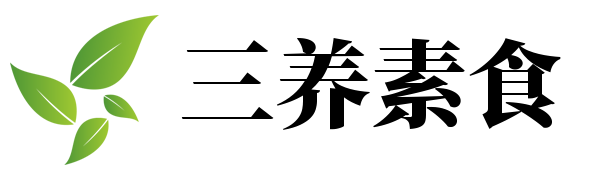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