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隽: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义
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注:分别见铠庵、吴克己:《释门正统》卷二,《新纂续藏经》(以下均简称《续藏经》)第75卷,275页;怀则:《天台传佛心印记》,《天台藏》湛然寺本,第188页。)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注:《释门正统》卷八,贤首相涉载记,《续藏经》第75卷,358页。另外,与天台的处境不同,华严诸师当时都颇受王权重视,如法藏为帝王所重,实称非虚;澄观也是帝颇敦重,频加礼节。(分别见《宋高僧传》卷5的法藏、澄观两传)天台为了建立正统,后来也有意识地与权力接近。)《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唐代华严所获得的胜利和正统性,迫使天台为了一争正统,也不得不开始重视到《起信》。被尊为天台九祖的湛然(711-782年)颇有焕然中兴之意,他深感道之难行,(注:均见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7,118页。)故而为了振兴天台,他也引述到当时华严宗十分推重的《起信》,并与华严作了不同方向的解释发挥。作为经师,湛然在解经中重塑传统,以期建立天台的正统性。(注:《释门正统》卷二中说,湛然注解《起信》,乃不满于贤首之疏不符佛祖大意,亦与《起信》之说相违背。《续藏经》第75卷,275页。另Linda Penkower也认为,湛然和知礼等天台学者热衷于通过诠注经典的方式来建立天台的新传统。见其,Making and Remaking Tradition:Chan-Jans Strategies Toward a Tang Tien-Tai Agenda,《天台大师研究》,平成9年3月1日发行。)从天台内部的传统看,湛然的思想尤得意于十门,所以他特别就天台的圆义创作了《十不二门》,该论逐渐成为后来台宗的经典。到了北宋,《十不二门》被天台学人视为辞实体要,览之使人见佛慧之渊,而于此争相诠释,但各家理解也发生很大的分歧,莫能一贯。(仁岳:《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56卷,第340页)天台内部所发生的山家、山外之争,虽然源于对《金光明经玄义》的广、略本之争,而思想的创造上,却与他们对《起信论》和《十不二门论》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非常深刻的关联。所以本文特别就这一范围来讨论山家、山外的所谓正统、异端之辩。
以正统性自居的山家有非常强烈的宗门意识,故其对山外的批判,多是以旧学天台,勿事兼讲的原则为号召的,(《佛祖统纪》卷八,《续藏经》第75卷,431页)处处以共扶正教,作传天台教观之院为己任,(注:分别见知礼,《四明十义书》卷下,《大正藏》第46卷,856页;《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五,四明付门人矩法师书,《大正藏》第46卷,904页。)在方法上,山家也通常把山外注经中的观念作为异端(heterodoxy),而有意识地牵连到华严的思想上面去,这点从志磐《佛祖统纪》为知礼所写的赞词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确:
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饰说,暨我宋隆兴,此道尚晦。故(晤)恩、(源)清兼业于前,(庆)昭、(智)圆异议于后,(继)齐、(咸)润以他党而外务,净觉以吾子而内畔,自荆溪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知礼)一师耳。
法登于《议中兴教观》中也说:
山家教观传来久矣,大小部轶典型尚在,独称四明法师中兴者,其故何哉?曰典型虽在而迷者异见,由乎山外一宗妄生穿凿,禀承既谬,见解复差,致一家教观日就陆沉矣。(注:重点是作者加的,引文均见《佛祖统纪》卷八,《续藏经》第75卷,432页;《议中兴教观》,《续藏经》第57卷,97页。)
有趣的是,北宋台宗内部对其思想分歧的叙述,似乎比来自外部的描述更激烈。如晤恩在天台宗史撰的纪录中是以他党而外务的异端,庆义在《重刻四明十义书序》中,也把晤恩说成是兼讲华严,不深本教,滥用他宗而使宗门大坏的人物。(《重刻四明十义书序》,《大正藏》第46卷,831页)但比照更早出版的,北宋赞宁《宋高僧传》(988年)卷七所记山外晤恩的传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晤恩被叙述成会昌法难之后,绍续天台正统思想的重要人物:
先是天台宗教,会昌毁后,文义残缺。谈妙之词,没名不显。恩寻绎十妙之始终,研敷五重之旨趣,讲大玄义、文句、止观二十余周,解行兼明,目足双运。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节语言荆溪记不相符顺,因著玄义、止观、金光明、金婢论科,总三十五帖,见行于世。(注:《宋高僧传》卷第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1,162页。)
不难发现,作为异端的山外学派,是经过山家思想家和史家的联手努力而逐渐被塑造出来的,应该注意到山家文献中的正统性意志和宗派意识形态的修辞。
为了建立自己一家之正统,山家不仅对内批判山外,对外诸宗的批判,也都特别联系到与正统性相关的问题上面。如他们一面吸收禅宗以祖统立教的方式,同时,在祖统相承的问题上,又特别务与禅宗相反,而批判禅家的祖统说。(注:宋台禅二宗之争,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2-125页;此亦可参见高雄义坚,《宋代佛教史的研究》,百华苑,昭和50年版,第80-87页。)对华严的批判,除了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特别运用到教学上的判教方式,因为判教直接关涉到宗派政治与正统性的地位问题。(注:Chi-Wah Chan,Chih-1i(960-1028)and the Crisis of Tien-tai Buddhism in the Early Sung,Peter N.Gregory,Daniel A.Getz Ed.,Buddhism in the Su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根据《释门正统》的纪录,台宗对华严诸师的判教有强烈的不满,如湛然就批评贤首五教的判定是有教无观,解行胡越,(注:《释门正统》卷八贤首相涉载记,《续藏经》第75卷,259页。)山家从义则对禅的祖统和华严宗密的判教都进行了广泛地料简。(见《续藏经》第75卷,324-325页)
北宋山家、山外的论争,多是以注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要注意的是,他们名义上是在注经,分歧也一般被叙述成理解或思想哲学路线上的不同。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够简单地应用一般诠释学的原则来分析他们的思想论辩,即不能够单纯地在经典文本与他们的解释之间找寻思想的关联。他们进行经典诠释的活动,还有重要的一面,就是要借经典来做事,解释活动的背后存在更复杂的权力关系有待进行系谱学(genealogy)的分析。如他们对《起信》的重视,除了思想上面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华严家用《起信》来建立自己一家圆教的地位。如华严宗的法藏就曾通过注解《起信》真如缘起的思想来进行判教。《起信论义记》卷上就把传译中土的一切经论,依教义的次第由低向高判为四教,即反映小乘诸部的随相法执宗,般若中观经论的真空无相宗,瑜伽行派经论的唯识法相宗,最后是包括《起信》在内的如来藏缘起宗。(《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上,《续藏经》第45卷,243页)虽然这里根据的是别种标准进行的判教,而不是华严一家特有的判教,但照法藏的解释,《起信》缘起论的依理起事,为华严提供了理事融通无碍的思想基础。
判教直接涉及到正统性的抉择,于是天台不得不对《起信》重新判释。山家知礼之融摄《起信》就有很明显地争正统的意思,其重要的目的是要借此批评华严和山外,故他有意识地把对《起信》的判释,与对华严宗的《起信》疏进行了区分,所批判的重点在法藏疏,而不是《起信》。知礼一面对《起信》作天台圆教方向的延伸,同时明确地以判教方式,把华严对《起信》的诠解判为别教随缘,而不是圆教。如他说《起信》为圆门而通别位,论以一心为宗,乃云总摄世、出世法,此则正在圆门;又说《起信》次第翻九相,乃为别位。而关于藏疏,他认为未能融合理具来谈缘起,所以立义望于天台,乃是别教一途之说,只能是别理:藏疏既未谈理具诸法,是则一理随缘变作诸法,则非无作。若不成无作,何得同今圆耶?(注:分别见知礼,《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二,第三,天台教与《起信论》融会章,别理随缘二十问,《大正藏》第46卷,871,875页。)这种扬《起信》而贬藏疏的做法,实际暗示了天台比华严更具有正统的地位。(注:安藤俊雄就认为,知礼判释《起信》与法藏疏有以华严哲学为别教的意义。安藤俊雄著,演培译,《天台性具思想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41页;)同时,天台内部各派也通过对《十不二门》的不同诠解,表示自己继承了湛然的道统。
从天台内部对《起信》、《十不二门》两论的不同诠释和争论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分歧并不象他们所表明的那样大,为了建立宗派的正统性,策略上必须有意识地制造出异端的共同体作为替罪羊。仔细地阅读他们有关哲学和宗教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不少所谓的思想对立是被虚构出来的。(注:陈英善在评论山家对山外的批评时就发现,知礼对山外思想的许多批判都是无效的,可说是种偏解及过度之推演所致。虽然她并没有指出知礼思想背后隐藏的宗派权力意识,但她发现知礼对山外的一再误解,可说某种情节所致。《天台性具思想》,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11,112页。)于是,注经不仅是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视野融合,意义已经不再是指向文本中所存在的东西,而更多地指涉到阅读经验中所发生的事情。解释作为一种修辞的策略(a rhetorical device),不再是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揭示,毋宁说关系到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旨趣对意义进行再创造(reproduce)。(注:Kevin J.Vanhoozer,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98,P158,167-169.)这一点,南宋了然在《十不二门枢要》叙中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诸家对《十不二门》解释,并非依文解义,而恰恰是安不由文,以意为主,悟意不侔,文随意变。(《续藏经》第56卷,364页)
De Bary在讨论中国乃至于东亚儒家正统性的观念时,曾提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正统性概念。(注:Kwang-Ching Liu,Ed.,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3-5.)借此来分析山家、山外的争论,可以说他们的分歧,从表面上看,都是围绕着哲学性的经典,就有关心性问题进行哲学的正统性(philosophical orthodoxy)辩论。而其实,思想的正统性并不是完全超然物外,纯粹独立的,思想合法性论争的背后隐含了超哲学的关切(extra-philosophical concern)和与政治力量的权力关系。(注:Linda Penkower在其即将发表的论文On Hermeneutics and Polemics:the Debate over Stone and Vegetal Buddhas中,指出湛然无情有性的思想背后所关心的,其实是佛教意识形态以及其宗派在社会权力中的关系。)正如Bernard Faure在分析禅宗祖师传统时所发现的那样,正统性通常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共同体为了成为正统性的一部分而制造出来的。(注:Bernard Faure,The Will to Orthodoxy: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9,180.)湛然如此,山家热衷于正统性的建立,力图抗折百家,超过诸说之谈,(法登:《议中兴教观》,《续藏经》第57卷,97页)也恰恰多少与其边缘化的焦虑(boundary anxiety)有深刻的关联。山外活动主要集中在钱塘(杭州),这在当时是中国东南之大都,为东南政治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地域;相对而说,山家所在的明州(宁波)则偏远的多。而且,连出自山家之后的《佛祖统纪》等史书也承认,在山家取得正统地位以前,山外的影响力远大于山家。后来山家为了谋求发展,特别协调与世俗政治力量的关系,因而表现出了他们对世俗社会所具有的高度热情与参与力。(注:较之山外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世俗事,不趋其(指大人豪族)门(《宋高僧传》卷第7,晤恩传)的倾向不同,山家显示了与社会权力之间积极的互动。此义可参见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399页。)对山家、山外之争的思想分析必须把对他们思想的哲学分析与系谱学的批判方法结合起来。目前大多研究天台的学者,重于思想的研究而忽略了系谱学的批判,故有意或无意地把宋以后台宗史书所形成的正统性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天台思想史的尺度。如日本安藤俊雄就以知礼一家的说法来判释整个天台教学的特色,并把山外视为天台正统的异断思想。(注:如以理毒性恶彰显自宗圆义,是知礼等宋以后山家提出的重要观念,安藤俊雄则用以判断传统天台的倾向。见《天台性具思想论》,第83,84页。又安藤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天台学根本思想的展开》(平乐寺书店,昭和43年版)中,就把山外描述成异端。见该书第14章,第一节。)宋代天台山家、山外之争,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基本被叙述成不同路线的思想斗争。所以本文在讨论山家、山外思想分歧的同时,特别注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各自建构其合法性的修辞和策略。
二、真如随缘与理事世界的再构造
本文并不是全面讨论北宋天台内山家与山外两派的论争,而主要择选他们有关世界构造的思想方式,以及相关联的实践方式(观心)等两个议题进行分析,以此批判地考察解释他们是如何在不同脉络的诠释活动中制造新的思想传统。
天台本来是不重视《起信》的,到了湛然,为了重振宗门,与华严相抗衡,遂参考到华严宗所依据的《起信》,特别是其真如不变随缘的思想。(注:安藤俊雄就认为,湛然于天台思想史上面做的一重要贡献,就是于天台教学体系中采用了《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见安氏,《天台思想史》,法藏馆,昭和34年版,第28页。)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把《起信》真如缘起论搬用到天台教学的体系中,而是有意识地作了与法藏不同的发挥。这一点已成为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注:如见吕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67,202,265页;安藤俊雄著,《天台性具思想论》,第148,149页;李世杰,唐代台宗的发展史要,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6,《天台宗之判教与发展》,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陈英善,《天台性具思想》,第10,12页。)《起信》真如缘起的说法还存在一些不太明确的地方,所以给各家解释以很大的空间。在法藏的疏中,缘起是结合着性起来说的;湛然并不想作这样的理解,而是要将天台性具的思想用《起信》来加以表现展开,于是真如随缘的思想问题被复杂化了。把真如缘起的思想引到天台内部,一方面是用以丰富天台本身的教义;但另一面,持有《起信论》的思想和用语,而要完全摆脱缘理真心的思想交错,这是不可能的。台宗内部的山家山外之争论,各固所是,繁于异论,杂乎粹旨,(处谦:《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显妙》,《续藏经》第56卷,356页)便与此直接相关。如安藤俊雄所说,后世山外、山家两派的思想,根本上可以解释成从湛然这种思想的二重性而展开的。(《天台性具思想论》,第158页)
吕征发现到了宋代以后,贤台两家关系就集中在《起信》上,自宗之内的分歧,也集中在《起信》上,这是很深刻的见地。(《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66页)而一般认为,湛然是在写作《金刚錍》时才用到《起信》真如缘起的说法来支持无情有性的思想,并批评华严宗对《起信》的解释。实际上,他在另外一篇重要的发挥智者大师《法华玄义》思想的《十不二门》中,也从台宗性具的立场,运用了《起信》缘起的观念。如在讲到色心不二门时,他以即心明变,变名为造,造为体用的方式来解释一切法无非心性的缘起观;于染净不二门的解释,也特别用《起信》中的水波之喻来讲性常缘起之理。(注:湛然:《十不二门》,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3-265页。)于是,当后来的山家、山外在讨论《起信》引出的问题同时,都纷纷重新解释湛然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十不二门》,原因即在于此。表面上直接解释自宗祖师的作品,而不是华严所重视的《起信》,这于沿承正统的方便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北宋山外、山家的争论,形式上是围绕着对湛然思想,尤其是他的《十不二门论》所发生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而实际思想方面的应用,却与《起信》存在深刻的关联。《释门正统》卷二的知礼传就说他信符《起信》宗,《佛祖统纪》卷八也说师(知礼)于《起信论》大有悟人,故平时著述多所援据。(均见《续藏经》第75卷,281,432页)
关于宋代天台内部思想争论的讨论,多少受到山家一系所建立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如学界仍然存在着简单以山外倾向《起信》、华严,讲性起;山家接续台宗正脉,重性具等观念来评判两系。(注:仔细研究山家、山外有关缘起义的说法,虽然他们有所不同,但所谓山家主性具,山外重性起之说是不能够成立的,这只是山家为了争正统而意识地制造出的思想斗争,详见下文的讨论。多是如吕征、安藤俊雄都认为山外的思想接近于《起信》、贤首,从天台性具说脱离出来。分别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67页;《天台性具思想论》,第186页。新近出版的董平之《天台宗研究》一书,也基本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山家、山外的争论。(见该书,第289,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也还没有摆脱这一影响,象Chi-Wah Chan论文Chih-li(960-1028)and the Crisis of Tien-tai Buddhism in the Early Sung,还是简单以《起信》、华严性起来看山外。)这一方面缘于山外的不少资料已经逸失,我们多从山家单方面的纪录中去看山家、山外的思想争论。包括南宋以后,山家系所建立起的天台宗史的资料(如《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都是以山家一家的观念来统摄天台教义。于是,对这些材料的应用,我们应该进行些系谱学的分析。另外一面,即使对现有的山外作品的读解,我们多半也受到传统天台正统观念的影响,而没有对问题进行更具批判性的理解。(注:陈英善的研究试图突破山家正统的看法,如认为山外对湛然《十不二门》的解释更接近湛然的思想,并批评知礼等山家很多诠解有违祖意。但陈的研究基本仍是在某家更符合正统性的观念下来判断两系的,见《天台性具思想》,第72,117-118页。我认为,我们应该打破正统性的观念,重新观察此两系是如何通过解释祖师的思想来为自宗合法性辩护,至于哪一系能够接续正统,则非单是思想的论争可以澄清,还涉及到背后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等观念的分析。)本文所涉及的有关《十不二门论》中缘起思想的议题,山外的作品多有保留,我们可以比较集中地来看他们各自的解释策略。
山家、山外争论的重点之一,是围绕《起信》真如随缘的不同解释而开展的。形式上看,这是有关对缘起义的不同理解,其实,他们的思想分歧,更多的不在思想本身,而是解释共同体试图在解释中表现自家的正统性。山家挑起缘起义的问题,是所谓别理随缘,即是说,这不单是对真如缘起作思想的解释,重要的是,这一解释涉及到判教方面的别、圆之争。(注:《佛祖统纪》卷八,知礼传中说,知礼于于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门指要钞〉成,立别理真如有随缘义,永嘉继齐立滥以难之,谓不变随缘是今家圆教之理,别理岂有随缘。(《续藏经》第75卷,430页)山家后学法登在《议中兴教观》中也说以山外一派宗天台者,咸谓贤首之宗大乘终教所说随缘,正同今家圆教随缘之义,挤掐本宗圆顿之谈,齐彼终教。(《续藏经》第57卷,97页)实际上,山外所解《起信》随缘并不是走华严性起的路线(见下文分析),山家虽然与山外对缘起有不同的解释,但每每有意识地硬把山家与华严联系起来,这一策略的效果是很容易造成一种假相:山外游离于天台正统之外。)于是双方的论辩难免充满意气,并形辞藻,互相攻击。(《释门正统》卷五,《续藏经》第75卷,319页)他们都在以自己的解释策略来改造《起信》,以争法统。这一点,山外的智圆说得很有意味:有四明知礼法师者,先达之高者也,尝为天台别理立随缘之名,而鲸吞起信之义焉。有永嘉继齐上人者,后进尤者也,谓礼为滥说耳。繇是并形章藻,二说偕行,如矢石焉。(注:智圆:《闲居编》卷二十一,与嘉禾玄法师书,《续藏经》第56卷,第897页。)
一般都认为,山外缘起论上走的是华严真心性起(nature origination)的路线,此一看法是很有问题的。山家、山外在缘起观上面的思想差别并不全象山家所说的那样,对立成为护持正统性的符号,而为山家有意识地放大了。山外派的源清解十不二门,成为山家批判的重要文献之一。源清广引《起信》随缘义,细究其文解,并非简单之真心论(ontology of true mind)。如他虽然认为一念心体是自性清净,一一法界法,即一念真如妙体,类似的说法在他解释十不二门的《示珠指》中还有不少,但这些说法基本都是指性体本净,即是从理体上面来立论的。所谓又此一念,体常虚寂,非念趣为明,非无念为静。念即无念,当体叵得诸法本来常寂灭相。(《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08页)关于这种偏指清净性体的倾向,源清有他自己的解释。在一段不太为研究者们注意,却相当重要的解释《起信》真如缘起是否为从真起妄这一真心论原则性的观念时,他作了这样的理解:此乃是佛起缘之说,不可定执是真是妄,何者?佛欲示诸众生,令其了妄即真故,云从真起妄耳。(《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10页)显然,从真谈缘起并不代表源清实际的主张,而毋宁说那是教化众生的一种权法和方便。源清重视的是于妄即真,这与山家所批评的缘理断九并无关系。关于此,山外智圆有更明确的辩护。智圆提出,山外一家所立心性之意,不同常途别立清净真如无生无漏,而是即妄而真,通于真妄的。他敏感地意识到山家对山外的批评,并非要坚持传统天台的圆义,而是有意识地偏指妄心为境,偏立妄心为解行理事之要,以保持与山外的区别。所以他批评偏真偏妄,俱非法义:若圣若凡者,圣即真心,凡即妄心。若唯真心,则离妄有真,如避空求空,是故不可偏指清净真如也;若唯妄心者,妄心遍计,诸法永殊,何名唯心耶?应知烦恼心性本具三千,即妄而真,体常周遍。(分别见智圆:《金刚錍显性录》卷二,卷三,《续藏经》第56卷,532,533,540页)
山家有关圆、别分判的观念其实是有多重变化的。就随缘义来讲,知礼为了料简华严性起和山外思想为别教,而提出别、圆的标准在于理具。他说若不谈体具者,随缘与不随缘,皆属别教。又说故知他宗极圆祗云性起,不云性具,深可思量。又不谈性具百界,但论变造诸法,何名无作耶?(知礼:《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下,《大正藏》第46卷,715页)我们通过山外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对缘起的解释,并不能够说是华严性起思想的一类。山外解《起信》缘起,处处沿用湛然以来理具的思想路线。如源清对《起信》无始无明的解释,恰恰就是从性具方面加以延伸的。他解释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一念本具十界诸法,清净圆湛。迷来无始,故曰本迷。是无住本具一切法,故称法性,由性本具,缘能生之染缘,能生染法;净缘能生净法。(源清:《十不二门示珠指》卷上,《续藏经》第56卷,309页)智圆也提出,教义的圆、别不在于是否讲缘起,而在是否坚持天台性具的立场:
当知他宗明圆得在唯心,失于心具。近人不晓,乃谓华严、起信宗师所谈圆极但是今家别教者,谬之甚矣。
应知今言真如随缘等者,永异他说,以他但云清净真如,不知真如具三千法。若非本具,云何能造,由内故,他境能熏,是知真如常熏内具。(《金刚錍显性录》卷二,《续藏经》第56卷,534,535页)
这完全符合知礼说过的然即理之谈,难得其意,须以具不具简的原则,(注:《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二,释请观音疏中消伏三用,《大正藏》第46卷,872页。)表明知礼试图以理具来分判他与山外的缘起观,这一点不能简单成立。
《起信》以说一心二门论缘起,一面说真如、生灭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又在心生灭门内说心有两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此意颇费解。天台分别以具来解摄,以造来说生,以此与华严性起路线相区别。从台家的理路看,言心具,必当以造来解缘起,这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谓色从心造,全体是心。此能造心具足诸法,若不本具,云何能造。(注:智圆:《闲居编》卷十,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正义序,《续藏经》第56卷,880页。)湛然开始以造来解释《起信》中真如缘起和体用的观念,当知心之色心,即心名变,变名为造,造谓体用,(湛然:《十不二门》)这一说法,后来成为天台一家的定论。北宋天台解《起信》真如随缘义,基本都在湛然的格局里作文章。被批判为偏离湛然路线的山外,对缘起的解释,其实也正是以造释变,即以天台本有的一念心造来改变华严性起的思想路线。关于此,源清有详密的解说:
真如性随缘,《起信》真如随缘义是也。《止观》大意云,随缘不变,名性不变,随缘名心。今言心即真如,性不变也;之色之心,随缘也。文(指《十不二门》)云变造同三者,唯圆为示。迷真性体,起惑业,苦相也。即以变释之,以造释变,以同释体。
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当知心之色心,即心名变,变名为造,造为体同,是则非色非心,而色而心,唯色唯心。(《十不二门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318,314页)
结合《起信》的缘起来讲性具,实际上并不是山外的创造,而是湛然所为,如湛然于《十不二门》讲染净不二时,非常明确地表示刹那性常缘起理一,一理之内而分净秽。(湛然:《十不二门》)于是,山家为了进一步区分与山外的思想,又以别种标准来衡论缘起的别与圆。如知礼就承认荆溪既许随缘之义,必许法性无明互为因缘,所以他主张随缘的别圆之别,并不只是判在理具这一观念(这是针对华严解《起信》而立的别、圆标准)。有鉴于山外讲随缘变造,偏向于性具理造的路线,如智圆所谓故观所造,唯见理具,不见诸法;(注:智圆:《闲居编》卷十,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正义序。)又说事为所造,而无能造:色等诸法既皆由心变,终成所造。(注:智圆:《金刚錍显性录》,转引自陈英善;《天台性具思想》,第135页。)山家于是提出,圆教与别教随缘的区别在于,别教只讲理具性造,而不讲事具,事造。为此,他们特别提示和发挥出所谓理事互具的观念,并要以此来作为正统性的根本。在山家看来,即使要说随缘变造,也要理、事平等,而非但理变造;山家批评山外虽然结合随缘谈心具,但不识二造,(注:知礼:《四明十义书》卷上,《大正藏》第46卷,841页。知礼后学善月于《山家余集》卷中的性恶义条中,亦以此意区分山家、山外之别。如他认为知礼说具不唯具性,亦具于相,故曰山千皆实,相相宛然,而山外之说则异乎是,言具则但具于性。《续藏经》第57卷,214页。)一味从上而下的只见理具,而不见事具,只讲理造,不重事造,因而还是有重真心的危险,而不是台宗一家所说的圆义。圆教的随缘是俱事俱理,应知若理若事,皆有此义(指缘起变造义)。为此,知礼还批评山外解释《十不二门》之心造,是局在于理,直作理释而不知道内外色心俱事,皆随缘故。(注:引文见知礼,《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大正藏》第46卷,711,710,708、709页;《四明十义书》卷下,《大正藏》第46卷,846页。)
仁岳解释十不二门的文心解虽是他与知礼分裂之后的作品,但他对真如缘起的看法并没有转向或接近山外的源清,而仍然坚持了山家的某些重要观念。(注:有学者认为仁岳《十不二门文心解》转向了山外真心路线,与源清等接近。见陈英善:《天台性具思想》,第64-66页。)
如他也特别批评了山外局于唯心来讲性具,而主张非但唯识,亦乃唯色、唯声、唯香、唯味等来讲互具。(见其著《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341页)他也批评山外不立事具,偏于真心:所以遍观所造,唯见理具故,云造谓理同;若言体用,但得从理变事之谈,而失指事即理之义。(《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344页)
仁岳甚至比知礼更彻底,他有时试图在解释湛然心之变、造的思想中,回到湛然以前的天台传统,抽去其源自于《起信》的一理缘起的观念。不过,策略上他把对这一观念的批判集中在山外对湛然的理解上。仁岳意识到山外并非不讲心具、心造,他认为山外的问题出在其把《起信》真如缘起的思想引入到性具思想的讨论中,可能会造成真前妄后之性起论的倾向,从而难显心为造法之本。在他看来,真如随缘还是别理,天台传统论理事相具,是当体即是的关系,须于一尘一念,不前不后而论具耳,章安明一念具十法界,云法性自尔,非作(缘起)所成。(《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341页)
与此相关的是对《十不二门》中法性与无明关系问题的解释。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起信》留下来的。真如在《起信》一心二门的构架中分别贯穿于理(真如门)与事(生灭门)两个层面。但《起信》本身有关这两门的关系说法,隐含而曲折。(注:《起信》在真如门内说真如有两种义:如实空与如实不空,但这里都没有直接谈到真如有缘起的意思,如说如实不空为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只是讲到心生灭门才说到有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的阿黎耶识的作用,而产生、变化出一切法。那么,生灭门中的不生不灭的真如与真如门中常恒不变的真如究竟是什么关系?《起信》没有表示,于是才有各家不同的解释。吕征就认为《起信》融会诸说而成,本身有许多矛盾未曾解决。如真如生灭两门中都有真如,其真如的性质和作用就说得很含混。见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0-201页。)《起信》各疏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早在六朝的净影寺慧远所作《起信论疏?卷上》就罗列过两种不同的解释,(参见《起信论疏》卷上,《续藏经》第45卷)此不详论。照法藏的理解,真如可以从两个层面看,究其真如门而言,是非染非净,非生非灭,不动不转,平等一味,性无差别的;而就生灭门的真如看,其又有随缘起灭,随熏转动,成于染净的意义。(《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中,《续藏经》第45卷,251页)依藏疏的看法,真如虽然分在不同层面,但这并非说有两个真如,而是同一真如分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而已。也可以说,同一真如有两种义:一不变义;二随缘义。随缘转动,乃由于无明的作用,无明亦二义,一无体即空义,二有用成事义。(《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中,《续藏经》第45卷,255页)无明熏习而使不变真如落于生灭门内;而无明体空,又表示法藏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中是坚持了真性一元论的立场。(注:此一点为华严非常重要的观念,法藏对《起信》的思想发挥,一再强调了真如之外,不得别立无明作不善体的思想。(引文见法藏,《大乘起信论别记》))因此一切法的流转(变、造)或还灭,都是真如理体自身的活动结果,经验世界或事的世界是被虚拟化成为真如活动的场所,其自身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山家显然不同意藏疏以真如自身的运动来解释一切法的缘起,而主张《起信》之谓生一切法,就可以从生灭门中的和合识来解释,而不需要牵涉到真如门的理体去说,这就是所谓指事即理的事具与事造。所以仁岳在解释《十不二门》有关法性之与无明变造诸法一句时,认为有的版本删去与字,乃是妄有除削,而主张与在这里非常重要,它表示了染净和合,因缘而生的意思,法性真如并不是本身可以独立的随缘派生,而是与无明和合才能够缘生一切法,唯真不生,单妄不成,真妄和合,方有所为。(注:仁岳:《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348-349页。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知礼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他基本认为,不管是否有两与字,其基本意思并没有分别。他不同意源清把法性之无明或无明之法性的之字解为往,而认为这纯粹是语助词。他说法性与无明的关系是一体两面,当体既互转翻,成于两用的,他们之间的互为因缘,不能单纯从理或事一方面来理解。如果释之为往,就会招从心生法之过。见《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下,卷上,《大正藏》第46卷,716,711页。实际上,知礼的批评,是指对着性起说的,这并不适合用于指源清的本义。源清这里重在以一元论讲圆教,并没有违背性具思想。如源清专门说到,夫十法界者,全是一念。非谓前后相生,诸法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当体相即的;关于无明之法性,源清也并非如知礼所批评的,指往之义,而正是此一念体常虚寂,非念趣为明,无明与法性之间是当体叵得的。(均见其《示指珠》卷上,《续藏经》第56卷,308页)有关此争论,还有学者从染净之间的感应关系去进行分析,此可见Brook Ziporyn,Evil and/or/as the Good:Omnicentrism,Intersubjectivity,and Value Paradox in Tiantai Buddhist Thought,Boston: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20-222.)就是说,山家是主张平视真如与生灭二门,反对单从真如理体来从上而下地横贯形上与经验面的世界,倾向于经验世界的本身具有变、造的功能。山家认为,只有从染净和合的经验面来看世界的缘起,才是台宗圆教的真义。仁岳的说法不仅是针对华严的藏疏,更直接地是批判山外,特别是源清对十不二门的解释。
我们可以分析下源清的说法。虽然源清坚持了天台性具的立场,但他认为现象世界是不能够独立于理体世界而自存的,相反,现象世界的染、净不是彼此独立的二元,而是真性一元(monism of true mind)。他说浊水之波清水之波,二波虽殊而湿性无殊。喻迷悟缘起虽二,唯心不二。若达不二之体,则了染净不二之用。这种迷性非体的一元论确实与华严立场非常相似。(引文均见《十不二门示珠指》卷下,《续藏经》第322页)所以在解释湛然《十不二门》法性之与无明变造一句时,源清坚持与字是衍出的。他担心,多一与字,就变成真如与无明共造一切法,把无明视为外来共法性和合的一种独立实体,这种二元论(dualism)是有违圆教的思想。源清对《起信》的接受是有所选择的:他一面吸收《起信》以真如缘起的方式来谈心具、心造,却拒绝《起信》以生灭门内染净和合生一切法的说法。是有别行本,加两与字,云法性之与无明,复云无明之与法性。若言之与,即语助与犹共也,乃是法性共无明造恶也。或引《起信》八识与染净相和合故,起染习种子等。他担心,这种和合可能导致的二元论有背于天台圆顿之法谈迷说性,不辨教之权实体别。(《十不二门示珠指》卷下,《续藏经》第321,322页)
实际上,别、圆在山家与山外的思想争论中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思想分判。《起信》在真如随缘的思想中,把法性与无明,即形上的理世界与现象(事)世界之间的过渡,通过无始无明和忽然念起的说法,变成了唯佛穷了的终局假定。(见《起信论》)于是,如何解释论文中的法性与无明的关系,并不能够找到确定的文本支持,而只能够从自家预设的前提中内在性地获得自圆其说。圆、别之判,在于各自对法性与世界关系之所给出的解释力。
从义学上看,这里有关自性或真如本性的规定只能是一形上学的断定(assertion),而非论证(argument)。如山外以为,心造必须回到真性一元的绝对主义,把无明销归于真如,削除妄染的独立存在性,才可能说是圆融的;山家则坚持敌对的相即为圆教的特色,即保留住真妄和合的经验性,才是究竟的,(注:山家讲性具,反对真心论,但亦不主张二元论,如知礼论法性与无明关系时,也引《起信》、《十不二门》以来常用的水波之喻加以说明:若论本具,平等一性,则非真非妄。虽则有清有浊,而一体无殊。清浊湿性者一体无殊也。又谓真妄关系是二无二体,真则全妄之真;妄则全真之妄。(见《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四,《大正藏》第46卷,891,892页。)这一说法,细究起来,与源清的真性一元略有区别。知礼讲的是真妄一元论,即性体可全真为真心一元,亦可全妄为妄心一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还涉及到对山家另外一重要观念理毒性恶的理解。当知礼以理性本具善恶来显示自宗圆义的时候,他如何统一他自己所主张过的一元论。此问题当另文讨论,这里无法展开。)两说各执一是。问题是,如果把一种形而上学的执见普遍化,并以此作为决定正统与异端的标准,那么这种我见就非常的危险。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如果我用我的空间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来冒险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那么就可能由于一种假象引起一个严重的错误因而是对一切可能的经验的有效的东西,当成普遍有效。(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54,55页。)这样看,山家、山外真正的分歧更多是各自形上学的不同断定,而不在哪家更符合佛意。两宗只是形上学的预设立场不同,而在不同的前提和脉络里,他们的论证都可以成其圆说。所以北宋天台学者遵式就说各家注解十不二门者,各陈异端,孰不自谓握灵蛇之珠,挥弥天之笔。(遵式:《十不二门指要钞?序》,《大正藏》第46卷,705页)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一本属纯粹的哲学争论是如何巧妙地被联系到别、圆判教的脉络中来进行的,这表示山家、山外两系,在构造世界秩序的同时不只是在进行思想的论辩,也在重新安排宗派话语和权力之间的次序。我们发现,山家不断变化着它对圆、别判释的标准,并希望把这些标准普遍化,这都说明对正统性的追求决定了其思想的制造方向,而不是相反。
很清楚,我们不能简单说,山外沿着《起信》、华严的思想路线,走向天台思想的异端,而山家则继承了天台的正统。与其说山家把别理随缘视为《起信》以来的别教观念,不如说其为了建立互具事造的思想,实际上把《起信》真如缘起的观念作了不同于华严,也不同于山外方向的延伸。山家与山外通过解释湛然的《十不二门》而分别发挥《起信》的思想,他们为了自家宗义建立的需要,在对同样经典的诊释策略中均有不同的抉择和偏向。这种同源异流,如果不进行细密的文本分析与批判,是很容易被正统化的台宗史家观念所简单化的。可以说,正统性的思想内涵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创造过程,自湛然引《起信》而重建天台,正统的天台观念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山家也正是在制造而不是在沿续一种正统性。
三、真妄观心?文本的批判分析
北宋天台内部有关观心(contemplation)问题的论争,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并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但我发现,这些研究有不少仍然是在山家一系的说辞中来论断两家的观心之争,最一般的结论是,山家重阴识,由妄而真;山外向理,直观真心。问题是,这种山家一家的说法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山家、山外对观心问题的争论据说是始于《金光明经玄义》广略本的讨论,但现存山外有关《玄义》中观心问题的意见,我们只能够从山家一家转述的资料中才能够看到,于是,对山家的叙述,我们应该保持批判性的眼光。代表知礼思想的《四明十义书》,是知礼的第一代孙继忠指受门人编辑而成的,(注:见《四明十义书》,十义书序,《大正藏》第46卷,832页。)其中所述两家观心义都是非常明确而对立的。如文中所记早期山外的思想基本都是纯谈法性,不立观心的,故而才为山家一系建立正统性制造了必要的异端。所以知礼的问难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教扶宗的意义:既知但教无观,乖于本宗,乃将教代观,而曲救之。值得注意的是,《十义书》中在观心方面判释正统与异端的标准是根据论敌思想的不同而变化的。针对早期山外,如晤恩等解《金光明玄义》,不立观心,而正论观法,的示行门,以贬斥山外的有理无行;而针对源清等山外所提出的观心义,又提出真、妄观法的区别,以观妄念为宗,自立门户。知礼就以拣示识心为境,而以此判山外观心为别教:缘于真心修观,正当荆溪所拣,缘理断九,义归别教。(均见《四明十义书》卷上,卷下,《大正藏》第46卷,832,833,835,848页)
从《十义书》中,我们很难准确了解山外观心的旨趣,从现存山家和山外有关《十不二门》的解释作品,如知礼的《指要钞》,仁岳的《文心解》,可度的《详解》,源清的《示珠指》,以及宗翌的《注法华本迹十不二门》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山家在十不二门的解释中,特别作了观心方向的延伸;而山外则倾向于实相和缘起两方面的发挥。如针对湛然《十不二门》开宗明义,曾提到观心乃是教行枢机这样一句话,这在源清的《示指珠》中几乎没有被提到,宗翌的注解中,也只是非常简单的几笔带过。(见其《十不二门注》,《续藏经》第56卷,326页)但在知礼等山家的解释中,却作了详细的发挥,并引以为十二门论之中心。知礼在《指要钞》卷上的解文中就说盖一切教行皆以观心为要,皆自观心而发。(《大正藏》第46卷,704页)仁岳也在他的释文中,大讲由阴入观,以第六王数为发观之始的唯观心论。(《十不二门文心解》,《续藏经》第56卷,340页)实际上,天台论观心,主要于止观义中详加发挥,湛然注解的《十不二门论》,其中心并不是围绕着观心,而是在实相、缘起等义方面。所以源清在解释该论时,就把重点分别放在不二唯心实相和迷悟法界缘起两个方面,(《十不二门示珠指》卷上,《续藏经》第56卷,308页)可以说这更切近该论思想的要义。而知礼的《指要钞》一面就缘起义的理解上批评山外的解释是别理随缘(如上文);另一面又要在《十不二门论》的解释中大加发挥观心之义,这很可能是有意识地针对源清解释的重点,别立宗义。
知礼对《十不二门论》解释中所刻意增加的观心之义,其实更多地来自于《起信》与《止观》等其他的经论。如他以《摩诃止观》的说法去立行造修,拣入理之门,起观之处,(《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大正藏》第46卷,706页)并借此批评山外的忽略观心,乃是重解不重行,有违祖意正统。又如他在《指要钞》中建立观心之义,而明确表示山家的观心宗旨是观一念无明心。而这个一念无明心是从《起信》生灭门中的和合识引申出来的观念,这一点,知礼也是公开引《起信》来证成己说的:此文正是于阴修乎止观,故《起信论》云,一切众生从本以来未曾离念。今释一念,乃是趣举根尘和合一刹那心。(《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大正藏》第46卷,707页)可见,山家的解十不二门,发挥观心一义,是别有所图的。这种在解经中再造意义的方式里,隐藏了更深的修辞策略。
山外在《十不二门》的解释中不详观心,并不表示山家不重观心行门,也不是象山家制造出的山外那样,是直云真性,偏指清净真如的。(《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大正藏》第46卷,706,709页)智圆所作《金刚錍显性录》(1006年)即是与知礼争论《金光明经玄义》期间(999-1006)的作品,虽然该论略晚于《指要钞》(1004年),但可以比较系统地反映出当时山外观心方面的主张。这里,我们并不要对智圆的观心论作详密的分析,只是就其即妄而真的观心入路,来简要说明山外的观心法门,与知礼的依阴心显妙理并不二致。(《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大正藏》第46卷,708页)山外于十不二门的解释虽不重观心,在于他们认为台教祖师的论典是鼎分部轶,翼张教行的,即不同论典有不同的重点,有的重论教,有的重论行,而彼此之间是相互应承的关系。智圆在《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正义序》中就说教在玄文,行在停观,意令解行相济。在他看来,天台有关行门的观心,主要是在《止观》之中勤勤点示的。(《闲居编》卷十,《续藏经》第56卷,880页)提到《止观》中的观心,《显性录》中是这样解释他的一家所谈:
今家所立,离真无妄,离妄无真,指无明心即三谛理,故《止观》观乎阴心烦恼心病心等,皆成不思议也。须知一家所立心性,即妄而真,若解若观,其理咸尔。
一家所谈刹那妄心,即三谛理,具足三千依正之法,唯在《止观》阴境之初,至于诸文曾未点示,良以《止观》是己心所行终穷之说,如此之观,名诸法源,不同偏指真如,以异一切唯识。(《金刚錍显性录》卷二,《续藏经》第56卷,532页)
从山外自己所叙述的观心论来看,所谓山外直观真心的说法,很可能是山家为了正统性的需要有意识地虚构出来的。那么,夸大思想紧张和对立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关系值得我们去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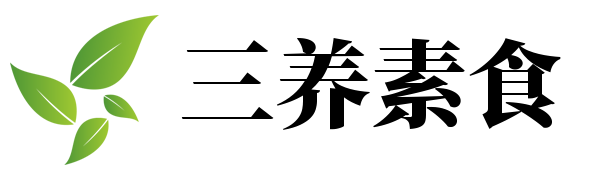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