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妈妈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爱妈妈来到这个世界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
只有母亲温暖的怀抱,才是我一生的企盼啊。而所有的叛逆与反抗,只是希望她能够多多关注我,喜欢我,并且,疼爱我。
至今仍然记得,与母亲大吵一次之后,自己躲在小小的厢房里,隐在一侧,听着母亲在外面焦急的大喊大叫,一个人急匆匆地向胡同深处走去的情景。
那年,我七岁。
正是十点的深夜。
到现在也不明白,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怎么就那么狠心,听见母亲去而复返的脚步,焦虑得带着哭音的呼唤,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
只是那么,静静地站着,任两行泪肆意的流淌。
有时候想,脾气太过相似的两个人,在一起,到底可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福。
哪怕是血脉相连的骨肉至亲,母女。
尤其,当她们的脾气同样火爆,同样不肯为了一点点小事退让低头的时候。
即使,她们同样深爱着彼此。
小时候,母亲永远是我不可亲近的一个。
也许是因了她对哥哥的偏疼,也许更是因为过于相似的暴躁。
母女两个人,仿佛永远也不可能平平静静地说一句话,往往是几句话没完,便大吵了起来。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而争吵的结果,是数不清的皮肉之痛。
一个母亲,以她母亲的权利,因女儿的桀傲不驯而不可扼抑的愤怒,将所有的伤心与痛苦借着手中的武器,愤愤地加于她女儿的身上。
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日渐一日的疏远。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也根本不知去想,为什么,一个母亲,会这样对待她的女儿。
血脉相连,骨肉至亲,如何会到这样一个地步。
而在这段历史中,作为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任性妄为的女儿,我究竟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而只是固执而叛逆地反抗着。
和哥哥一样,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不足月。
哥哥是六个月多一点,而我更惨,还差几天才六个月。
母亲的血样极其特殊,她根本没有能力将一个孩子连续十个月地保护在肚子里。
按正常来说,她的血脉,根本无法养住一个孩子。
真不知道,三个孩子,她是冒着怎样的风险,以怎样的坚毅,生下来,并且,将我们兄妹两个,健健康康地养大。
也许因为哥哥是第一个孩子,母亲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会有这种事情存在,因此在哥哥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
由于先天的严重不足,加上母亲最初的不善照顾,自小哥哥的身体便很虚弱。
那个时代里,所有的资料都极度匮乏,母亲的身体还根本不适合去做一个母亲,哥哥自小便是那种极粗糙的大饼干泡白水做奶水,仅有的一点营养,是父亲早晨四点便去粮店排队而凭粮票抢购回来的一斤牛奶。
因为这一点,母亲对哥哥,一直怀有极深的愧疚,与疼爱。
直至今日,仍然记得幼时和哥哥伏在温暖的炕沿上,两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看着父亲守在炉边,将铝制的饭盒放在旺火上煮的情景。牛奶烧得滚滚的,一点淡淡的牛奶油脂渐渐浮起汇聚,哥哥的眼睛便紧紧地盯在其上。
火势极旺的炉子旁,父亲的额角,那一层密密的汗珠仍宛然眼前。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姊姊出生一年之后。
而且也正是姊姊死后的那一年。
姊姊的走,完全是个意外。
而与先天的虚弱无关,尽管她也才六个多月。
姊姊十三天的时候,邻居领着她幼小的不足三岁的女儿到我家里去探望母亲。母亲与女孩的母亲不远不近的扯一些闲话,而那个小女孩,就那个时候走到姊姊的旁边,与姊姊哇哇地交谈,不知所云。
不知什么时候,她一下子坐到了姊姊的脑袋上,母亲发现了,惊得大叫。
另一个女孩的母亲,一下子吓得不知所措,怔怔地坐了一会,见姊姊还知大哭,呼吸顺畅,便舒了口气,借故离去了。
没过三天,姊姊便去了,母亲说是吓的。
说这些的时候,已是许多年后,她的口气很平淡。
因为一个疼爱之极的儿子,因为一个早夭的女儿,母亲极想再要一个女儿,乖巧、体贴,听话,会哄人。
我就带着这样的企盼,来到这个世界。
只是不如母亲的意,我是按照她的复制品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照她的意愿,乖巧可爱。
而当愿望失衡之后,脾气的暴躁可想而知,尤其是面对一个同样脾气倔犟不知低头不懂事的女儿,会是怎样的失望,与伤心。
与母亲的明争暗斗,持续了十几年。
(如今回头想来,那十几年的岁月,本应是母亲最焕发光彩最美丽的十几年。对于一个女人,一个结婚生子日渐成熟的女人,这十几年又是怎样的美丽与珍贵。)
尽管我们,深深地相爱着。
即便,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有我爱她,而她的心里,就只有哥哥一个。
但是我仍然不可否认,我爱她,真正的,深切地爱着她。虽然一张口,两个人之间便宛如有一层冰障般寒冷。
从来没有人,如我那样的深切地关心她,在意她,为她去做我可以做到的一切。
哪怕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自小疼爱的哥哥。
也许,男人照顾家人的方式,真的是那样粗糙,不经意吧。
只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在关切她的同时,却又满怀着不被她疼爱的不忿。所有的感觉加在一起,只是觉得一种付出感情却不被回报的伤心。
从来没想过,一个母亲,何曾想过去要她的女儿回报给她些什么。
生活的担子渐渐压弯了母亲的腰,母亲光洁的脸上也已经渐渐有了皱纹。
那个时候,父亲是县里砖厂的一个班长,母亲则是县里造纸厂的一个职工。
国营和集体的称呼,自小便是父母和我们常做的一个游戏,问我和哥哥,谁接爸爸的班,又有谁,接母亲的班。
后来,所有的不景气遇到一起,两个人的单位几乎是同时垮掉了。
父亲作为一个男人,一时之间似乎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是母亲最先振作起来,以她的一贯强硬与偶尔展现地精明做起了小小的生意。
父亲在那时开始酗酒,直到现在。
近二十年的时光。
母亲凌晨两三点,开始起床,推着一辆农用的车,很重,就一个人在天还根本漆黑一片的时候,推到离家门远隔几条街的蔬菜批发早市,又一个人,将车放在一旁,辛辛苦苦地去挑选各种形色和价格都合适的蔬菜,往往在五六点钟才匆匆赶回离家很近的那条街,在街口摆起菜摊。
一个女人,怎样撑起一个家庭,而她,究意要付出多少?
尽管,她也许真的称不上柔弱。
可是一个女人的最深处,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强悍的男人的关心,与照顾。
为了这一点,十几年来,对一直深深疼爱自己的父亲,始终抱有怨言。
尽管,对父亲这许多年来的无语疼爱,始终感激,并且,无以为报。
那时我很嗜睡,毕竟还小。
可是没过两天,母亲起床的声音,还是吵醒了我。
如今具体地想来,并不是那些母亲刻意掩盖的细微的声音唤醒我,而是母女相连的骨血至亲,让我总觉得有些什么东西放不下,适时地醒来。
记得第一次强迫自己爬起来,睡眼惺松地走到母亲身侧,帮着她一起推车时,母亲眼角闪动的泪花。只是,她还是不曾说出,她的感动,以及,她是爱我的。也许,一直以来,她都没有这个习惯。
而那个时候,也不懂,母亲的泪,是怎样一种深切的爱意。
到了菜场,我就守在推车旁,母亲便放心地去挑她的菜色,往往在她回来时,给我捎上一点自己特意买的桃子,时新的柿子,或者其它的小零食。
六点钟,回去收拾书包,我便背起书包,往自己的学校走去。
那个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
一直到初二,母亲才结束了摆菜摊的生涯,开始卖水果。
而那段时间,最常的事,便是放学时,到母亲的菜摊,将书包一甩,就替母亲卖菜,收钱。
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单独做生意,也是在这段时间。
那个时候,小小年纪便自以为自己有了生意头脑。初夏的日子,七月初,桃子刚刚上市,我便从母亲那里讨了一笔钱,宣称自己要单独做一番大事,从父亲的一个做水果批发的朋友那里搬来了一大筐桃子,八十多块钱,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因为怕水果熟透容易坏掉,加上桃子刚刚上市价格偏高,怕销路不好,还自作聪明地挑了一筐才微微泛些红丝的青色桃子,以为过几天,就会全部熟好,正好耐卖。
那筐桃子,我摆在离家一条街的十字路口,整整卖了一个月才将近卖完,几乎耗近了整个暑假。
确实地说,原本应该卖一百多元的一筐桃子,卖了一共也没有十几元钱,余下的桃子,由原来的碗口大干缩到了有桃仁大小,还是我和哥哥边吃边卖,才勉强了事。
惊奇的是,一向严厉的母亲,却出奇地没有责怪心虚的我,只是呵呵的笑着,说,这么小的娃娃居然也会做生意,赔了没关系,就当我买了筐桃子给你们做零食吃了。
由最初的零售,到与阿姨合伙的批发销售,母亲又花了几年的时光。
也不知糊里糊涂地怎么就混上了高中,而且还是相当高的分数,害得一票朋友又是欣羡又是不屑。
说也奇怪,由于自小陪母亲的早起,养成了在教室上总是精神恍惚,加上眼睛一直不是很好用,根本看不清课堂上的板书,只知一人神游物外,浑不知老师在课堂上忙些什么。
只是偶尔从同学那借来笔记,做一些临时的补充,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了大学毕业。
高三一年,经历了对母亲由抱怨到感恩的两个极端。
尽管自小的经历养成了相对偏激的个性,加上天生的倔犟,但是仍然让我保持了对很多事情的淡然与冷静,处理事情时分寸总是恰到好处,以及为人极端的自立。
就像从改自己的名字,初一自己决定休学时由自己去找老师打点一切,中考时自己在高中与中专之间的抉择,高一时的文理分科,直到高考的志愿填报,所有应该由父母做决断的事件,事关自己人生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我自己去做的选择。
不是抱怨,而是早已习惯,并视作理所当然。
因此,在初入高三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对我,是一个多么关键的人生阶段。而父母,应该在那时对我做些怎样的关顾与引导。
直到快高考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所谓独立及与家人的疏离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而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母亲一面了。
而三个月前,还是由于功课不紧,我去租好的库房里看望母亲。
看到别人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体贴备至,尤其是到一个朋友家里时,看到她母亲对她的百般维护及看管,以及因我的到访而担心会分她攻读之心的敌意,都让我在那一刹那间感觉到,有时候,琐碎,是一种怎样让人心痛的幸福。
为什么,我的母亲,就可以安心地把我扔到家里三个月之久,在我高三差几天就要高考的的时候?
直到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也没有见到母亲。父亲偶尔回来一次,也没有带来任何这方面的叮嘱。
毕业后与同学连续几天的饮酒,加上父母在外面的库房居住,哥哥又因父母不合多年一直借居伯父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何其难得的一个清静所在,家里便成了同学往来的一个聚居点。
直到哥哥领了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嫂子回家,父母才一起回到家里打理。
嫂子那时还不能叫嫂子,第二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有很大影响的事件,一向胆大妄为的我,从此开始惧怕起一切黑暗的东西。
深夜里,快十一点了,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在街边的商店买好的东西顺着幽深的胡同往远在几十米外的属于自己的家里走去。
当我尖利的叫声刚刚划破了深夜的静谧,甚至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只是下意识地尖叫时,隐隐约约地一片杂乱的声音霎时之间自家门口传出,身后的黑影松开卡在我喉咙的手,转身慌乱地跑掉了。
第一个冲出来的居然是一向不睦也很少交流的哥哥。事后嫂子说,跑出来的时候,他居然连鞋也没有穿,就那样光着脚追了几条胡同,才因担心我而急匆匆地赶回来,双脚上划了几个口子。
还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软到了母亲的怀里。只听到母亲焦虑的呼唤在耳侧隐隐响起。
那个夜里,我一直只想沉沉睡去,而母亲,一直流着泪,捧着我的脸,唤我起来,不让我睡。
虽然只是受了惊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可是母亲那焦虑的面庞,在那一刹那,分外的亲切起来,我仿佛找到了惟一的依靠,倚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倦得只想入睡。
原来,只有母亲温暖的怀抱,才是我一生的企盼啊。而所有的叛逆与反抗,只是希望她能够多多关注我,喜欢我,并且,疼爱我。
她生平第一次打了我一耳光,对着她担心到骨子里的女儿,只因怕我睡着。受到严重惊吓的人是绝不能立时睡着的,应该保持相对清醒的状态,加上亲人的抚慰,才有可能恢复心理的正常。妈妈事后说,她根本不敢让我睡,怕我醒来之后,造成长久的心理伤害。
父亲和哥哥嫂子忙里忙外,给我煮姜汤,在我身侧忙来忙去,而母亲,只是紧紧的搂着我,一个人靠着冰冷的墙面,用她的体温和颤抖着的轻声细语,引我说话,振作起我的精神,其他所有的事情再不是她关注的对象,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她受惊吓的女儿身上。
母亲,她是怎样深切地爱着她不肖的女儿啊!
大一初报到,是我第一次离家在外。
临行前一夜,一向强悍的母亲,坚持要亲手给我收拾行囊,在她整理一些路上带的东西时,手竟然抖了起来。
一滴清泪,滴到了她刚刚锁好的皮箱上。
原以为她会去送我的,但是凌晨起床后去汽车站前,轻轻唤了母亲一声,母亲闭着眼睛,静静睡着。
父亲和哥哥送我,几个小时的路程,看着身侧的父兄,想起前一夜母亲的落泪,竟默默地哭了起来。
母亲也会落泪的啊。而终究,她是没能送我。
许久之后,哥哥悄悄给我打电话,说我走的那天早晨,嫂子看到母亲一个人爬起来,怔怔地望着我远去的方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都是泪水。很久很久。
从此之后,每次我的离别,似乎都是母亲泪水涌现之时。
别的学生寒暑假都未必会回家一次,只有我,每年的国庆,五一,寒、暑假,一年的四次回家,是必定的行程。
大一后,系里规定每个暑假前我们都要出外实习三个礼拜,然后直接放假。当大家自己安排实习地点的时候,我却早已跑到了家里,守在母亲的身旁。
对着她们的讥笑,我只是淡然以置。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依恋母亲的怀抱,我想把这许多年来亏欠母亲的,以及这许多年中有意无意错过的母女之情,都在我所能把握的时间里,尽数的还给,及珍视。
我明白,在我首次离开家里时,一向强硬的母亲,便似乎在突然之间垮了下来,变得软弱而善感。
非典肆虐之际,母亲一天一次的电话,催问我怎么样,催我在火车上安全的时候回家一聚。
忽然想起九八年那场大洪水。暑假里连续半个多月的暴雨,加之水库的不堪重荷,所有的一切岌岌可危。那个时候家里已经建起了离地面两米高的小小平台,希望在洪水来时有一个栖身之地。
母亲起初不肯让我去学校报道,哭着说,一家人,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可是开学半个月前,洪水最危急的那个时间,听说第二天铁路公路就要封了,母亲急匆匆地和父亲强行将我架上了即将开启的火车,目送我远去。
她说,长春毕竟是长春,离洪水相对较远,你在那里,可以很安全,我很放心。
她的泪光隐隐。
父母之爱,有时,可以深沉若斯啊。
有时候想,母亲这一生,实在不能算是幸福。操了太多的心,也吃了太多的苦。
如今,尽管儿女不再须她操心,却由于父亲的酗酒,夫妻两人的生活几十年来都不甚和睦。子孙守在身边还好,可是最不放心的女儿,却仍在远她千里之遥的外地。
我所能做的,只是几个月后,在保证不会给小小县城带去什么危害的前提下,到家里,去看望母亲。
即使离别时,还会见母亲的泪。
只因为在浪费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是为爱这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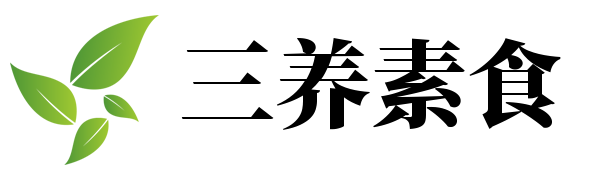




















评论